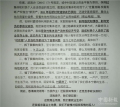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很多美好的事物总会不期而至,它是善意的微笑,它是温暖的拥抱;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些并不美好的事物亦会如影随形,它是良善的泯灭,它是正义的迟到。
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了农村妇女秋菊为了向踢伤自己丈夫的村长讨"说法","一根筋"逐级上告的故事。看完影片我们发现,自始至终,秋菊要的"说法"只不过是村长的一句道歉,因为她认为村长"不对"。

近年,湖南邵东农村大娘谢恩求也是因为认为社区书记邓某喜等人"不对",与他们"怼"上了。为了举报邓某喜等人在征地过程中的诸多违法行为,为了讨回一个"说法",她抛家舍业,带领村民数次进京寻求真理。
是的,对一位农村妇女来说,判断一个人、一件事,"对与不对"就是她心中最朴素的标准。
谢恩求原本是一位本分老实的女性农民,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过着面朝泥土背朝天的日子,未曾走出大山,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她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收,而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自己的利益被邓某喜等人肆无忌惮地掠夺,明显"不对"。
在她看来,这种"不对"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邓某喜等人利用自己掌握的职权,大肆侵占和掠夺包括她在内的众多村民的利益:邓某喜于2007年12月26日未经原湖塘村现新辉社区车禾组、冒家组、中古组、前进组四个小组组长和村民小组签字同意,私自签订征地协议,强行以每亩34000多元的价格征收四个组33.45亩预留地,再以每亩800000元卖给开发商明珠集团,从中牟取暴利25087500元。让人惊讶的是,即便征收价格低得离谱,分到四个组的补偿费用仍未按照实际征收的33.45亩计算,而是少分了6.27亩的补偿费用(折合人民币213180元)。此外,邓某喜套取四个村民小组田基瓜墩240余亩折合人民币6720000元、套取安置房32间折合人民币10240000元、套取迁坟款2250000元等共计52510689元。
其次,在诉求的过程中,她和受害村民多次反映问题,非但没有结果,反而处处被邓某喜等人粗暴打击报复。他们多次到省城、到北京寻找“青天”,却被邓某喜等人百般阻挠,乃至设计陷害,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拘押。这让谢恩求很不理解,她怀疑邓某喜等人背后有着隐蔽而强大的"保护伞"。
此外,这几年,自己明明掌握着邓某喜等人违法乱纪的证据,却状告无门。反映的问题,不是被推诿扯皮,就是被踢皮球,她举报的违法违纪的"不对"之人却岿然不动,没有得到相应惩罚。
气愤与怨恨,让这位年过六旬的农村大娘走上了无奈之路。谁能将她拔出泥潭?谁能让正义早一点到来?谢恩求在渴求,湖南邵东的众多失地村民在渴求!
诚然,我们很难相信,法治大潮滚滚,一个小小的社区书记竟能兴风作浪,动辄贪污千万;我们也很难相信,扫黑除恶风疾雨暴,各路"保护伞"们竟敢只手遮天,不辨黑白是非。
然而,当看到一位文化种度并不高的农村大娘写出的长达13页纸的控诉材料,当面对一位农村大娘抛家弃业、忍饥挨饿乃至不顾生死数次进京探求真理的事实,我们是否应该有所反思: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农村大娘充满了挑战腐败权力的勇气?她所举报的问题是子虚乌有还是真实存在,为什么迟迟没有让人信服的处理结果?
当下乡村社会,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不断上演着超乎人们想像力的各种荒诞剧,芸芸看客,皆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主义者、为着利益熙来攘往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没有人关注卑微若蝼蚁的这位农村大娘。
这让我想起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在《我没有话说》一诗中所写:纳粹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不受制约的权力面前,人人皆为蝼蚁,非正义之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中产贵胄。
承受苦难者不应该被漠视,制造苦难者不应该被宽容,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当他人身陷泥涂,我们应该拉他起身。
愿天下再无农村大娘抛家弃业去奔波,去呐喊。
(赵英杰)
附谢恩求、姜平华举报材料(部分)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