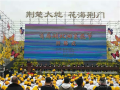文、李根萍
青枝绿叶果儿长,辛辣甘甜任人尝。在赣西萍乡,辣椒一直是家中餐桌上的主打菜。如果那顿饭中少了辣椒,肯定食之无味,大打折扣,总觉少了什么。没了辣椒,主妇真不知这个菜如何炒了;少了辣椒,这个日子不知如何过了。
辣椒是生命里的火焰,没有辣椒,就如火红的玫瑰,失去了艳丽的色彩,不再鲜活灵动。随便走进萍乡谁家的厨房,灶台上肯定有罐红彤彤的干辣椒粉,酷似江浙人家灶台有罐必不可少的糖一样。
最早吃辣椒的是葡萄牙人。然后,辣椒一路向东,沿着葡萄牙的贸易线路,传入马六甲、泰国、日本、朝鲜和印度,继而从朝鲜进入中国。亚洲是最热情的食辣区。而中国,是最辉煌的辣椒之国。
中国现存最早的辣椒记载却出现在浙江,杭州人、戏曲家高濂写于1591年的《遵生八笺》。以及1598年汤显祖的《牡丹亭》。这两处记载都是着眼于辣椒花。农业文明遗产专家王思明教授根据地方志进行的研究发现,在康熙年间,最早出现辣椒记载的是浙江,其次是湖南和辽宁。
故乡萍乡位于江西的西部,湖南的东部,毗邻湖南醴陵,是声名远扬的食辣市。“贵州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而萍乡人是辣不死,辣死人不偿命,不是不温不火的辣,而是地地道道的武辣。数百年来,辣椒在这里成为一种文明,深植在乡亲的血液里,流淌成一种霸蛮之气。辣椒,造就了萍乡人的性格:勇敢、大气、热烈、豪迈、坚定、执拗。吃得辣、耐得烦、把得蛮、不信邪,是萍乡人身上的印记。过去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萍乡人:吃下一碗辣,敢把地球抖三下!
每年清明时节,赣西大地上的风硬冷,早晚气温低。父亲等不及了,总是早早地将宛如肾形黄色的辣椒种子,小心翼翼地撒进了湿润的地里。为让它早点从土里钻出来,父亲用竹片在地垄上搭成个半圆形的棚子,再用塑料薄膜盖个严实,让辣椒种子在里面做着香甜的美梦。白天,春风唱着歌儿从棚顶拂过,似是在对它们的召唤;阳光热情地亲吻它们,让它们天天沉浸在幸福的时光里。
大约半个月后,大棚里发生了变化,种子如笋破土,黑色的地上争相冒出密密麻麻的嫩芽来,你挨着我,我挤着你,宛如幼儿园一群小朋友在运动场上奔跑。有时白天温度高了,父亲还会将塑料薄膜掀起来,犹如挽起一袭漂亮的公主纱裙,裙子里晃动着一个个绿色的小脑袋。不过晚上温差大,还是要盖起来,不然会冻坏嫩苗。因温度适宜,土质肥沃,浇水勤快,辣椒秧子在大棚里疯长,不停地窜个、长叶,绿油油的。清明过后,大棚里留不住它们了,它们要迁徙了——移栽到另一块土里去。
一般辣椒种一茬就要换个地方,要么就换点新土,因为辣椒根系发达,喜欢认生土,越是首次种的地方越是长势好、产量高,主要是它们成长需要足够的肥料和营养。移栽辣椒前,父亲比种其他蔬菜重视得多,因为这是家中的主打菜,关系一年餐桌菜肴的丰盛,甚至关乎一家老小生活的质量。他先是反复筛选种辣椒的地方,多半会扫点落叶,烧点草木灰盖在上地面。然后,用羊角翻地,让土暴晒几天,把土里的细菌和虫子晒死,继而整平、挖好坑。一行三四个或是四五个坑,横竖大抵对齐就行,但不能靠得太近,距离有讲究,因为辣椒苗需要透气,更需要充足阳光雨露的照耀。
选个雨天或是傍晚,父亲就会将连根带土的辣椒秧子,移栽到早已准备好的一个个坑里,再给每棵秧苗浇点水,以利它在新地方尽快适应扎根。开始几天,如气温较高,每天早上都要浇点水,不能让秧苗因温度过高而夭折。
移栽在地里的辣椒秧晃过神来后,长得很卖力,个儿越长越高,茎也变粗了,这时肥料要跟上去。每施一次肥,它就会窜高几寸。辣椒的叶子呈椭圆形,叶片的顶端尖尖的,叶子嫩嫩的,煞是好看。时光从菜地里飞逝,两周后就能看到辣椒的枝丫像手指一样叉开,开始长成树的模样,白色的花苞从枝枝节节上嘟噜嘟噜地冒出来。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像一个个细小的星星,连着一个稍微弯曲的绿柄,埋在碧绿的枝丫间。不几天,白色的花朵便洋洋洒洒,叶子的光芒黯淡了下去。
总是在一个早上,父亲踩着晨曦在地头巡视庄稼时,忽视会发现辣椒苗上结出辣椒来了,犹如水稻开始抽穗,果树开始挂果,这是令人兴奋激动的事情。米粒儿大小的它们,宛如初出家门的小姑娘,满脸羞怯,总想寻求叶子的庇护。田间地头,山坡路旁,其实没有谁会常去打扰它们。于是,它们在黎明破晓时分,或是在落日黄昏间隙,悄悄地长个子,沉甸甸地往下坠,绿色的叶子下面,满眼皆是下坠的一个个小辣椒。
倾情不怕千刀碎,佐料尤调百味丰。端阳节前后,地里辣椒越结越多,越长越大,有的竟然有食指粗了,每棵苗上都有一二只大的辣椒,十分诱人。此际辣椒的味儿极为稀薄,温顺得像怕老婆的男人,又软又嫩,一点也没有火辣的性子,仅有一股蔬菜的青涩味儿。用乡亲们的话说,食之如同吃青菜,辣而无劲。我性子急,每年都喜欢吃头茬辣椒,总是急不可耐地下到地里,摘回一碗辣椒,让母亲将鲜嫩的辣椒一刀拍碎,再加蒜头清炒,这青涩微辣的味道,同样能让我过个瘾,吃上几碗米饭。
丽质生身菜圃中,少时葱绿老来红。待到盛夏,烈日当空,辣椒宛如过门后的小媳妇,出门被人一逗,红了大半个脸。这个时候,地里的辣椒尽情吮吸着肥料养分,个儿粗壮,一半火红,一半碧绿。不规则棱形的辣椒叶绿得滴翠,仿佛绿丝绒上镶嵌着无数的红宝石、绿宝石。一串串,一排排,悬挂着,酷似孩子般荡着秋千。这样的场景,父亲看眼里,喜在心头。炒菜没它法,辣椒来当家。母亲总是开心地提着菜篮子,踩在晶莹的露水,下到地里摘回辣椒。手中有辣,心里不慌。那些日子,家中餐桌上花样百出,辣椒炒鸡蛋、辣椒炒小炒肉、辣椒炒鱼干、辣椒炒腊肉、辣椒炒鸡肉……家中菜谱里,每道都有个鲜红的辣字。
母亲喜欢用辣椒炒干塘鱼,这道菜端上桌,香气四溢,让人味蕾翻滚。我和二哥小时候不太吃辣,但又禁不住小鱼儿的诱惑,便舀碗凉水,夹条小鱼,先在水里涮涮,这才小心翼翼的放进嘴里,味道显然差远了。三个姐姐特别能吃辣椒,她们用只大勺子,麻利地挖勺辣椒鱼干,拌着饭一起吃,吃得津津有味,故常笑我和二哥,不像个萍乡人。
后来经她们一激,我有了勇气,也学着挖勺辣椒往嘴里塞,只觉得嘴里冒火,脸似红布,肚子鼓得像沟里的气蛤蟆,可小手还依然不停地在辣椒里找鱼干。鱼干没了,就干脆夹起了辣椒,用一大口饭来陪着吃。不知是鱼的诱惑,还是遗传了父母亲吃辣椒的基因,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竟然觉得辣椒并没想象中的那么辣,那么可怕。伴着幸福的饱嗝儿,我甚至还感觉到有一缕热乎乎的辣香,带着骄傲的成就感,悠悠地浮上来,有味极了,仿佛日子都是甜的了。父亲见六七岁的我,就能吃上一小碗辣椒,连连夸赞:“小子,行了,有种!”
那些成长的岁月,尽管家中不富裕,甚至缺油少盐,但辣椒的香味慷慨无私地弥漫着家中的餐桌。辣椒给了我好胃口,给我了浑身的力量,让我养成了辣一样的性格。
地里的辣椒红了,母亲就会带着我用大草篮子摘回,洗净泥沙,放在晒谷坪上晒。火红的辣椒摊开在雪白的坪上,犹如山里孩子扯下一片朝阳,特别扎眼,映红了田野,映红了池塘,映红了山村,映红了乡亲的日子。辣椒晒干后,装袋贮存起来,待冬春季食用。这两个季节,新鲜辣椒没了,家里多吃辣椒粉。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一场苦霜过后,万木消瘦,北雁衔凉,辣椒也放下了喧哗和躁动,耷拉下叶子,开始暗淡,辣椒也瘦小了许多,这个时候的辣椒成之为谢苗辣椒。意思为辣椒苗快要凋谢的辣椒。此际的辣椒,辣劲不足了,但炒小炒肉味儿不错,尤其是拍碎加蒜头做成垫辣椒,味道堪称一绝,是下饭神菜。
“这从大地之中提取的火焰,它是我们亲人中的亲人,它与我们形影不离,相伴一生,在舌尖上燃烧的熊熊大火,与我们一起走过轰轰烈烈的日子。我的亲人们在最苦的时候,喝完一大碗火红的辣椒,大喊一声:雄起!辣椒流进血液中,站立起来的辣椒!……”这是诗人对辣椒尽情地赞美。品格刚毅情如火,意志坚强性更浓。萍乡乡亲就是这样,天天与辣椒形影不离,相伴一生,因为能吃辣椒,一生敢走四方,做人坦坦荡荡,有话直来直去,从不遮遮掩掩。
光阴似水,白驹过隙。我在异乡漂泊几十年了,可无论品尝哪儿的辣椒,都没家乡这个味儿,更没家乡的劲儿。有时想家了,为过过辣椒瘾,常常找遍大半个城市,但每吃一次就失望一次,无法找到故乡吃辣的感觉。早些年有个江西人在大院对面的东大影壁开了家赣菜馆,还设了个萍乡厅,一度人气火爆,每天都有江西老表在此相聚。后来,因店家经营不善关门了,甚是遗憾。每次回萍乡,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到地里,摘碗新鲜的辣椒吃吃,找回童年的感觉。每次返回,我都会带上一大袋新鲜的辣椒,存在冰箱里,慢慢地吃,细细地品,让故乡的味道多保留长久一些。
辣椒,对于我这个游子来说,其实是抹不去的乡愁。“覌君入口仍含笑,保你出名誉满城。历代豪杰都喜爱,餐桌少我怎能行。”历代文人墨客赞美辣椒的诗,其风流蕴藉之味,不亚于余光中的《乡愁四韵》。
常有人问我,最想念故乡的是什么?我总是张口而出:辣椒!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