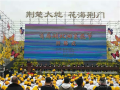内容提要:丁玲的一生是自强与创作的一生,她不断地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在20-40年代中,其创作依次主要表现分别为:女性独尊意识,女性对主导文化的认同和女性的自强意识、性别意识。她先后获得了个性、政治和文化三个观照层面,使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纽结中产生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变。
丁玲,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以其特有的真诚和感触关注着妇女问题,表现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世界,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同时又在时代大潮的推涌下产生了政治热情,并力图表现时代精神,高扬政治意识,使创作中的性别特征逐步消解。在她一生的创作历程中,随着人们的意识的觉醒、阶级意识的萌生和性别意识的出现,她先后获得了个性、政治和文化三个观照层面,使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纽结中产生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变。
一、女性意识的起点与高扬
20年代,“个性解放”开始向“阶级解放”过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及大革命在国民党右冀背叛下失败于血泪之中,使一大批激进的知识分子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意识到“五四”时期鼓吹“个性解放”是空幻无力的,懂得“不消灭阶级,就达不到个人的真正自由”,从而转向对阶级解放的谋求。早在20年代中期,郭沫若就反省了自己的思想:我从前是个尊重个性、信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也认为先前信仰的进化论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者助官捕人的事实!茅盾、叶绍钧等人还塑造了由“个性解放”走向“阶级解放”的“时代女性”的形象。梅行素(《虹》),金佩璋(《倪焕之》)不以爱情和个人幸福为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将自身解放同社会解放联系在一起,“负起历史的使命来”,“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丁玲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背景下走向文坛的,但是她的思想却明显落后于时代,她虽有革命的愿望,却对革命缺乏深刻的认识,只是沉溺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梦幻中,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现实惊醒了她,使她从理想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尘埃,找不到人生的出路,陷入了“孤独的愤怒、挣扎和绝望。”①于是在其作品中,全力塑造出以莎菲为代表的女性系列,包括梦珂、莎菲、承淑、阿毛、小菡、志清、节大姐等,她们都是喜欢做“梦”而“梦”醒了又无路可走的知识分子女性。
在丁玲的创作中,她既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伤感和绝望,也代表了新女性对自我人格的珍视和为捍卫做人的权利而进行的精神反叛,丁玲用“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思想观照着妇女问题,由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妇女们发现了自己“非人”的处境,意识到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完全失去了自我,因而她们在“个性解放”思想的召唤下,以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为榜样,发出了“女性也是人”的呐喊,向束缚个性、压抑情感的漠视人的尊严的传统势力冲去。丁玲在40年代中期撰文指出:“中国妇女几千年来都在一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状态中延续下来。②这种认识代表了她对旧时妇女处境的一贯看法。虽然她没有在创作中正面揭示妇女“非人”的处境,但揭示了新女性的生存困境和苦难历程,表现了她们在自我意识觉醒后进行的精神扩张。
丁玲的女性意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与“五·四”的“个性解放”有着密切联系,不过,其内核与“五·四”又有一定的差异。从“五·四”那一代人来看,爱情、婚姻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是统一的,因此争取做人的权利往往首先表现为对婚恋自由的渴望。在“五·四”退潮后的20年代,觉悟了的女性虽然已从家庭走向了社会,但她们没有出路,又无所作为,只得徘徊于十字街头,彷徨苦闷,孤立无援。出于心理防护和捍卫自由的需要,她们以自尊低御了一切,表现出强烈的女性独尊意识。
丁玲笔下的女性也是自我尊严的自我维护者。莎菲尽管“颠狂于男人的丰仪”,却也提防着“男人的灵魂”,坚决拒绝被纳入传统文化,终于在狂吻了那男人以后,一脚踢开了他。此外,由于独尊意识的强化,莎菲们也特别期待别人注意自己,了解自己。梦珂挺身而出,制止“红鼻子”教员对女模特的非礼;在觉察晓淞绅士风度背后隐藏的邪念后,又毅然离去。较之于经济的丰足和婚恋的自由,她们更迫切地需要被社会承认,为社会所注目。
在表现女性的尊严的同时,丁玲也特别突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在莎菲们眼里,一切都是不屑一顾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失去了灵光,婚姻被看成了坟墓和囚茏(《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甚至被认为同卖淫一样,是女人堕落的合法形式(《梦珂》、《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男人则是粗俗之辈(《梦珂》、《小火车轮上》),是高贵的外形里隐藏着卑劣的灵魂(《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里,两性地位发生了明显的置换,女性不再意味着屈从和依附,而是置于社会的中心。体现了新女性为维护人的尊严而进行的心理反弹。
虽然这毕竟是心造的幻影,与当时妇女的处境和社会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但丁玲早期的心态却使她对妇女的精神充满了关注。她躲开了大革命后的阶级矛盾,在精神领域内遨游,表现了活生生的女性经验和复杂的情感世界。丁玲的早期创作虽然疏离了时代精神,但获得了“个性解放”的参照系,深入了女性的精神世界,表现并放大了女性的追求与苦闷,从而在个性的全面释放中体现了创作主体高扬的女性意识,对于漠视女性存在的男权主义者们,也是一个有力的闪击。
二、女性意识的弱化与消解
丁玲早期的创作“还未意识到一个基础的消灭有赖于整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根除……她在女主人公的形象里寻找着对妇女问题的解决,但这些女性在反抗中却是无力的。”③
20年代未,丁玲开始注意自己的文学与时代保持“同步”轨迹,这是她强烈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使命感在文学上的体现。三十年代初期,丁玲参加左联,丈夫胡也频牺牲后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主编左联机关刊《北斗》。她在斗争中意识到文学的重要性,自觉地调整自己与时代的距离,转换写作方向以适应中国革命的进行。她开始从狭小的感情世界中走出,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她开始将自我意识容入集体意识,女性意识溶入政治意识之中。由“个性解放向“阶级解放”转变以后的丁玲,对妇女有了新的理解。她认识到妇女首先面临着同男性一起反抗整个社会制度的重任,妇女的解放不可能脱离社会的解放而单独完成。不仅如此,还要放弃个人主义立场,走出旁观者的局限,自觉选择与大众结合的道路。基于这样的认识,丁玲放弃了自我的个性扩张,投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中,更多的从社会解放的角度探讨妇女问题,要求妇女顺应时代,用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解放。因而其女性意识被冲淡,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
在创作上,丁玲从个人主义的虚无走向工农大众革命的路。丽嘉(《韦护》)在革命的时代发生了思想的转变,由爱情至上和个人幸福至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成长为走向革命的“时代女性”。丽嘉“有热情、有魔力”,血管中“有着诗人的浓厚的苦闷”。韦护的出现,使她找到了情感的寄托,“她不愿意离开他,因为没有他,思想就没有主宰,生活便无意义了。”在经历了一番爱情幻灭的痛苦后,她还是振奋起来,否定了自我,表示“要好好做点事业”,“作为探索人生路上的新起点”。相反,玛丽(《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则是作为一个拒绝面向社会,拒绝承担责任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女性而受到了否定,从她身上丁玲表现了对早期人生观的反驳。
丁玲转向以后的创作丢弃了惯有的“革命加恋爱”的俗套。更多地表现了女性对主导文化的认同。三小姐(《田家冲》)不仅抛开了爱情,还背叛了本阶级,投入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曼贞(《母亲》)则告别旧式女子的生活,一步步“挣扎着从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④《母亲》弥补了《田家冲》在表现女性精神历程方面的不足,但两者在表现女主人公同革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与丽嘉和美琳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丁玲以高度政治化的心态,认同了同时代的“大众意识”,强调女性走向社会的人生选择,把革命当成人生的第一要事,而对妇女问题,特别是女性丰富复杂的心理情态,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这是与那时的革命思潮同步的。丁玲在诗歌《给我的爱》中表达了“大家都一样”的“红色”形态,没有男女之别,“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由于对时代主导文化的强调,丁玲的创作逐步走向了与早期不同的另一端。
从丽嘉(《韦护》)到三小姐(《田农冲》),我们可看出丁玲思想意识的运动,即政治意识的逐步强化和女性意识的逐步弱化。由于作家思想的偏激,且受“直接符合并服务于社会革命利益”的影响,一时难以单独对妇女问题进行单独的思考,即使表现了一定的妇女心态,也只是她们走向革命的心中历程而已。随着政治热情的高涨和革命工作的开展。丁玲产生了新的追求,因而失去了自我剖析的心境。这样,女性意识也就慢慢被政治声浪所淹没,以至被消解。到了《水》、《奔》、《法网》、《松子》、《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作品,探索性的女性已完全不复存在,而挣扎在贫困和灾难中的工农群像和投身于抗日工作的英雄人物,则基本上占据了她整个意识的空间。女性意识的弱化和消解,使女性丰富生动的精神世界被忽视,因而女性文学丧失了特殊性,而对想象中的革命活动的描写,又很可能会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她此时的创作也就因而失去了揭示灵魂的浓度和多样性,失去了富有个性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三、女性意识的回归与升华
30年代未到40年代初,丁玲的思想比较活路,一方面高扬着抗战的主旋律,表现“救亡”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又对30年代初的某些偏激作了调整,甚至有些方面体现了逆向的观照视角。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她创作了很多杂文,讽刺了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如《作家与大众》和《“三八节”有感》等。她开始放弃了30年代初的天真与狂热,重新思想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探求怎样的社会才有利于妇女的生存,使男女得以真正的平等,并使女性们的生活富有人的尊严。
在这痛苦的反思中,她的女性意识发生了回归。但它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已超越了早期的个性与前期的政治层面,比较注重于挖掘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背后的传统文化积淀。这时的丁玲产生了性别意识,认识到女性有着男人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容颜易老,青春不再,也难以抵挡诱惑,她们在生活中承受着比男人沉重得多的负荷。表面地强调男女平等,只能造成新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延安时期许多妇女被讥为“落后”便是例证。这表明性别歧视仍然存在,男性对女性有着很深的偏见,女性自身也有着长期被男性文化定义而产生的惰性,难以摆脱依赖性、软弱性和贞节观念。为此,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呼吁男人们要理解并新生女性,鼓励她们扬起生活的风帆,与她们互补互存,更期待女性们自我强健走出历史的阴影、实现人格的平等。希望她们“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和梦幻”,不要随波逐流,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等。
在小说创作中,她既表现了女性的自强意识,又提示了人物或环境中的文化积淀。《夜》批评了妇女的软弱性、依赖性与自卑心理。何明华的妻子很不能干,所有的农活都留给当干部的丈夫,还骂他“不挣钱,不顾家”。她需要的只是“安适的生活”,希望丈夫在她身边,做她的依靠,而对他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中极不理解,不懂得他到底要的是什么,甚至疑心他有“外遇”,从而成为丈夫事业的累赘。相反,《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则赞美了女性的自强意识,表现她们不为环境所困的倔强精神,同时也表现了弥漫于环境中的封建文化毒素。《新的信念》是30年代后期的作品,政治色彩较浓,但已露出了女性自强意识的端倪。《我在霞村的时候》表现了贞贞成为日军的妓女后如何带着满身的伤痛,走向新的生活,从而体现了“人的伟大和尊严”,⑤丁玲在表现贞贞抛开传统思想走向新生活的时候,也真实地揭示了积淀在群众思想意识中的封建文化成分。人们歧视她,躲避她,中伤她,骂她“比破鞋还不如”,是“缺德婆娘”。一些妇女甚至从贞贞身上看出自己的贞操还没被日本人奸污而沾沾自喜。丁玲以贞贞的生存困境展示了我们民族和革命中存在的麻木。沉重的贞节观念和缺乏对不幸者的同情心,真诚期望“解放区的村长们应当开展一场群众教育运动,使人们人道地对待那些不幸的妇女。”⑥《在医院中》既表现一个“千锤百炼而不消溶”的“女强人”气度,也提示了封建文化积淀中的对人的漠视。院长看介绍信就好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漫不经心;医院中“肮脏的秩序,设备不完善,病人营养差,用具破了无人管理,病房不温暖,大家忙而又闲,流言纷起”。丁玲高举着人性主义的旗帜,塑造了一个与官僚主义和传统文化作斗争的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女医生形象。
不过,在对敌斗争异常艰苦的时期,客观上要求大家同心同德,求大同存小异,最大限度地调动抗敌的积极性。但是,丁玲却把解剖刀举向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疽痛,与主旋律是多少有些不合拍的。为此,她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特别是《“三八节”有感》成为了批评的焦点。丁玲只得承认它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要争气的味道。在经历了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以后,她开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五十年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丁玲的创作中又一次呈现出单一的时代颂歌,如《杜晚香》是好人好事的赞歌,女主人公的心灵充满集体主义和工作热情,她超越了个人的苦闷,对丈夫的封建意识不以为然,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杜晚香的形象告诉人们,妇女“要取得平等,就得强已”。⑦然而,杜晚香毕竟是被神化了的,即没有内在的文化冲突,也没有作为女人的独特感受,成为时代精神的化身,使整个作品流于简单和肤浅,这大概是单纯的丁玲所始料未及的。
总体来看,40年代丁玲的思想虽然几经曲折,但她对女性注入了新的思考,揭示了妇女解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封建文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妇女如果不抛弃幻想,克服惰性,就无法与男人真正平等。
丁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中,一直对妇女的解放进行着执着的探索,她的女性意识是一条流动的河,跃动着她的生命和才情,也折射了她的思想和创作的曲折历程,她力图与时代一道前进,却有着一份对女性割舍不去的情愫。她是矛盾的,始终无法将两者统一起来,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其女性意识也随着两者的发展而呈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轨迹。
(华容县黄湖小学 付倩)
注:
①《丁玲文集》第14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版
②《丁玲集外文集》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
③⑤⑥《丁玲研究在国外》第55页、第191页、第45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版
④《丁玲研究资料》第2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版
⑦《丁玲文集》第4卷第39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版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