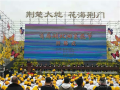文/宋扬
趣问一小孩:“米从哪里来?”答曰:“超市买的。”小孩的无知当然可以谅解,但作为成人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一粒谷子到下一粒谷子有多远?
“春雨惊春清谷天”,似乎到了清明前后就应该考虑谷子下种了。但农时的到来却是灵活的。如果打春在农历的年前,清明节就在农历的二月;打春在农历的年后,清明节又推迟到农历三月。“二月清明莫赶前,三月清明正种田”,农人对《二十四节气歌》的运用从来都不墨守成规,须得等到三月的清明,才是培育秧苗的最佳时机。
谷种先晒一晒,使其干湿均匀,出芽才整齐。然后放进田水或塘水(井水温度过低,碱性大)浸泡一整天,中途换一次水,最后把谷种平铺在竹笆上放入温室(煮饭后留着余温的灶口)催芽。沉睡的谷子在水分与温度的作用下开始慢慢苏醒。
与此同时,秧田的翻松与平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收割完油菜籽的春水田如同分娩后的母亲,元气的恢复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雨。春雨一般是温柔而娇羞的,好在还有哗哗的蓄水从高山上的湖泊流下来,春水田又活泛起来。水一润,耕牛就该上场了。犁铧翻起的黑色泥浪一层一层,犁铧白亮亮的耀眼,新起的泥光滑如镜如丝。水面上惊走的水蜘蛛和抱着遗落的油菜荚战战兢兢的蚂蚁,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震惊慌失措。老牛只笃定地向前,从不会想到甩掉枷锁揭竿而起。这只老牛是县上给我们生产队的奖品,理由是我们队的人均日劳动产值超过了一元钱,是全县生产队的翘楚。
一切的不安最后都被完美的归宿代替,蚂蚁在岸边找到新家,水蜘蛛从来不惧漂泊天涯。春水田被疯长的油菜秸秆根茎支离得凹凸不平的肌肤又平整如初,脸上红晕再生,她在等待下一场孕育。
“清明断雪谷雨霜”,虽然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夜晚依然寒意料峭,秧苗需要覆盖拱起的塑料薄膜保温。夜里覆盖,白天再掀开薄膜透气,让秧苗接受日光的适度呵护。
再过一段时间,秧苗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分家了,它们嘴上没唠叨,却以噌噌噌蹿高的个子宣告对脱颖而出看到更蓝的天空的渴望。分家意味着单门独户,自成一家,然后长成真正的稻子。插大秧苗的舞蹈如火如荼地上演,春水田就是最明净的舞台。水田五月的烟岚在晨曦中褪去,薄薄的水面开始倒影天光云影和飞鸟的踪迹,也折射出半酥软的土坷垃。明晃晃的水田里,插秧应该是技术活。只见父亲坐在“秧凳”上,宛如在春水田里划船。秧凳的发明者肯定没有学过物理学,却把“压力与压强”的知识运用得如此贴近民生。秧凳底座是一块两头微微翘起的木板,有了它,秧凳可以很省力地在水田里滑行。木板上面钉着一个有弧度、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木凳,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坐在上面的人的疲劳。只见母亲手起分秧,一落手,秧苗便直直地立在了田里,一起一落之间,水连成了一条弧线。我该如何去表达这个动作带给我的美感?是武林高手踏浪而来,脚尖撩起的水花;是柔曼女子依依裙裾牵扯出的线条……看得手痒,我也撩起衣袖,挽起裤角,跳进田里学插秧。然而我的处女秀硬是把直线推进搞成了逶迤蛇行。父亲一声断喝:“你这是搞啥子,滚一边去!”就把我赶到了一边。
在大人的怒骂声中我永远地失去了插秧的机会,只能眼巴巴望着他们在田里妙手翻飞。殊不知,插秧也是辛苦活儿,一天下来,大人们腰都直不起来。不懂事的孩子哪里体会得到这些?那闲置的秧凳早载着我在另一块田里飞翔起来,我和秧凳都是快乐的鱼。
剩下的,就是静静地等待。春水田是这个大家族的母亲,黎明的薄雾中,她目光脉脉,只希望眼前成排的万千孩子快快长呵!等到孩子们个个灌了清浆,胖了身躯,黄了谷壳,直等到嗡嗡的打谷机的声音开始在原野响起。
晾晒在晒坝里的谷子需要用“抓筢”捞去零零散散的稻草,用类似于《西游记》里猪八戒的武器一样的工具推平。这钉耙,于我们小孩而言可是疯打的最佳玩具。如果天气好,谷子一天就可以晒干过心,如果天气一般,需要连续晒两到三天。阴干的谷子做出来的米饭远不如在烈日下暴晒的谷子香甜。
早有一架风谷机摆在晒坝等着晒干的谷子。风谷机的顶部是一个大漏斗,一个摇柄和轴承带动叶片扇风。谷子里的土灰被吹得远远的,而那些尚可以用来喂牲口的瘪谷因为有一定重量被留在第二道出口,至于最饱满的谷子,当然乖乖滑进第一道出口的箩筐里。
精选的稻谷被倒入打米机,白花花的香米从打米机上如春水一样流淌出来,一粒谷子这才完成了从谷子到米的历程。
其实,谷子的成长过程远不止我所写的这么简单。看过《平凡的世界》的人就都知道主人公孙少安为了让村里的农田能得到救命的水,几乎把命都豁出去的艰辛。
那粒被留在谷仓中的谷种和农人一样,体会过生活的艰辛。日子有忧有喜,太阳照常升起。时光让它变得平静,它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轮回,静静地……
济慈在诗中写道:“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一粒谷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何尝不是大地上一首永不死亡的诗歌?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树的礼赞 唐海林/诗歌
下一篇:梨花青瓦相对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