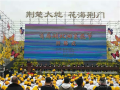小村的青铜时代
文/方君才
从紫草坞地铁口走出,已是黄昏,我再也找不到回沙窝村的路。
印象中,沙窝的房子不高,砖瓦结构,墙壁夯实,一天到晚有人吆喝卖毛鸡羔儿(孵化失败的鸡蛋)的声音,浓厚的北方农村气息扑面而来。村口的南坝河满是淤泥,冒着泡,大概里面蕴藏许多沼气。白杨树高高矗立乡道两旁,有着老北京乡下的气息。麦田里的乌鸦极多,黑黑一大片,也不怕人,在空旷地带跳跃。
出门时经常要路过曹薇家的土地,一百多亩,栽种的都是冬小麦,一眼望不到边。对于从小在湘西喝岩浆水长大的孩子来说,这自然有些稀奇,一到了五月,华北平原风大,麦浪翻滚,景致极美。多少年以后,我还能想起那种波澜壮阔的场面,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句子形容,或者,就像北方大炕,就像曹薇敞开的怀,让我着迷。
小村的青铜时代和一条人工河有关。
无数个夜晚,一大群少男少女坐在河坝弹吉他,草甸子柔软极了。这是小刺猬交配的季节,黄沙从盐碱地卷起,似乎都吹进了口齿,不干不净,但也不难受,丝毫不影响我们唱《喀秋莎》《橄榄树》,唱《外面的世界》《北方的狼》……一直唱到月亮落西山。
实际上,我不太想起曹薇的模样了,不是我有多么薄情,大约时光是一把杀猪刀,几乎要狠心地将她剔除在记忆之外,而我却又是如此难以舍弃。
也许,无法忘却的应该不仅仅是某一个人,而是一段青涩、永远回不去的时光。
不想把一件事说得太透彻,但我必须交代清楚这件事的始末。
认识曹薇,是因为曹四爷。认识曹四爷,是因为黄三。和黄三相遇,完全是因为我在西单无法呆下去了。
我在北京的几年,整天无所事事,还是饭来张口的那种。学潮过去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远,我是个得过且过的公民。我不关心大事。我只关心鲁冰花什么时候融化。我只关心北京什么时候下雨。
在北京工作的姨妈从不厌弃我,对我是当儿子待的。大约是我自己太寂寞了,她和姨父上班去了,表妹上学去了,我在家也闲不起,学了一段时间的五笔打字,慢慢讨厌了386黑白电脑。我想起了锻炼身体,于是每天大清早从大悦城跑步到公主坟,饿了,买一张馅饼、一瓶矿泉水充饥。折回家,我多半会散步,最喜欢就是穿过东交民巷的使馆路,那儿有很多漂亮的穿着暴露的外国美眉,在那儿散步,或者打羽毛球,使馆门口有警卫,虽然不能靠近,但还是可以赏心悦目。
我很颓废,戴着姨父给我的随身听一路播放音乐台,多半是靡靡之音。随身听是松下牌,可以在太阳下充电,这是一款时下不错的品牌,令我自豪!我记不清是在哪个街口邂逅黄三,他是我少年时的同学,也是老乡。他乡遇故知,免不了一番雀跃,然后是吹牛,话题也不下作,无外乎是哪个漂亮的女人看上咱了,哥们儿还不鸟她。我们从不谈理想,对于北漂一族,理想太奢侈。
黄三说,有一大群湘西人在朝阳郊区一个大型吊车公司上班,大家都住在沙窝村。这种工作很简单,就是随大型起重设备将钢板、电机、冷却塔等送到基地,或直接安装。小工的工作就是用缆绳将重物系好,指挥吊车司机起吊然后放下解绳。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工种的危险性,起吊重物如果没系好,特别是钢板,会发生倾斜事故,在下面指挥的工人十有八九会光荣。后来,我也去了这个公司工作,亲眼看见凤凰县竿子坪一个叫民权的老兄,被空中掉下来的钢板扎断了一条腿,这也是后来促成我离开北京的原因之一。
去沙窝,姨给我打包了厚厚两床棉被,当然还有一叠人民币,至今想来,老人家无非就是担心我在外面挨饿,同时让我在别人面前活得像个爷们而已。
我随身带有一把竹笛,它是我的好伙伴,也不完全为了虚荣心,它的确是我的爱好之一,虽然我现在再也没碰过竹笛,大约与心性有关吧!实际上,每天我都要练习一两个小时独奏曲。
沙窝村务工的老乡没什么娱乐节目,多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听我吹笛子,然后是村里的乐队成员盯上了我,一个是绳二三,一个是曹四爷。绳二三是弹键盘的,他一进门就问我会不会玩吉他,我说还可以吧。他给我介绍了同来的曹四爷,曹四爷娘肚里瞎,为了生存,他自小学会了弹三弦、吹笛子,天桥文化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北京,能被人称为爷的多半德高望重,曹四爷年轻时候一个狠角儿。虽然眼瞎,但人很聪明,朝阳区打架斗狠他多半是军师。曹四爷是村庄的智者,哪家哪屋有个动静,他都清楚。他的弦子弹得好,北京本土的说唱艺术也很有意思。
我在沙窝村白天上班,下班后就在乐队玩,村里的男女老少在广场跳交谊舞,跳舞的也有湘西的务工青年,我很轻松地融入当地人的那个圈子。
四爷没结婚,一个人住了个大院子。曹薇是他二哥的独生女儿,这一家的第二代不怎么旺盛,就是家里的地多,他们雇请河南那边的农民种小麦和玉米,收割后都卖给市场。我和四爷之间互动多了些,曹薇在一家大商场上班,话不多,天生的忧郁气质,每天下班回来都要给四爷送半只烤鸭。
我不属于那种客气的人,半只烤鸭够我和四爷下酒了。
“厚儿,你家兄弟姐妹多吧?”四爷问我。
“不多,三兄弟。”
“没亲事吧?”
我挤兑四爷,“年轻人不急。”
“你看曹薇咋样?”四爷认真了,“老曹家孩子心地善良,我看你娃聪明,你同意,我就给我二哥说一声,准成!”
我半晌不语,这婚姻大事得多大啊,我对婚姻还没概念。我记得曹薇的父亲是村书记,生得很威严,不苟言笑。
后来,四爷还是给曹薇的父亲说起了这事。“让孩子多处一处吧。”曹薇的父母没反对。
最初,我和曹薇在一起很腼腆。通常是沿南坝河骑单车,穿过一大片树叶茂密的白杨林,就到了一座草甸子。我们坐在地上,隔了一米以上的距离。她默默递给一个水杯,“渴了吧,这是我的水杯。”除去标点符号,九颗汉字,其中那颗“我”咬字很重,她的脸有些红。其实,我的表面看起来很瘦,其实生的很结实,不过是五六公里的里程,踩单车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不怎么渴,但还是接过杯,喝了一口。这是对女孩子的尊重,也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谁厌弃谁的感觉,有的只是陌生,但彼此还是渴望接近。所以那一口水我喝得很认真,尽管我没渴。
至今为止,这都是我第一次相亲。我应该相貌堂堂,虽然不是一表人材,但还是落了俗套。
这一大段记忆很难拼凑,而且很容易断层。二十年后,再次踏入沙窝村的土地,再也找不着北,四周高大的建筑物让人迷离,当年的小村庄已找不到旧时模样。霓虹灯闪烁,给我的感觉就像曹薇的唇,她是喜欢化妆的,北京郊区的女孩儿都这样。
沙窝村地处五环外,这个村庄最终也没躲过被房地产商开发的命运。我不知道房价多少钱一平,想必天子脚下,很多人打破脑袋也要往这儿挤,价格应该不菲。
在村里待了一年多,我一手拿烙饼,一手拿大葱,饮食习惯基本被曹薇一家同化了。
四爷非常满意我的改变。曹爸显而易见的高兴,他们家也接受我这样一个乡下野孩子的到来,每次上曹薇家吃饭,桌上的气氛很浓,牛栏山二锅头也容易见底。
星期天,曹薇会拉着我的手,去沟渠里捉龙虾,这玩意儿会咬人,我反倒没有她胆子大。她说她从来没去过湘西,认识我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后来她恶补了大量的湘西知识,才撅着嘴,“原来是出土匪的地方啊,怪不得……”
我知道她“怪不得”这层意思,怪不得我说话带脏字,怪不得我敢亲她,怪不得我喝酒了就敢在草甸子撒尿……但丝毫不影响她对我的好感。
当时,我是真的不喜欢这种风平浪静的生活,说白了就是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我想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种路是什么路,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想弄明白。但是,我和曹薇不可救药地相爱了,除了两者之间的海拔有差距,其他看起来都很般配。
我开玩笑地说,“薇啊,我想借一架梯子。”
“嘛啦?”
“想观察一下你的唇为什么那么红。”
她反应过来,莞尔轻笑,给我腰捅了一下,“高挑还不好吗?给你生一窝篮球队员。”
我认为,当时自己都还是孩子,曹薇要给我生一窝娃儿,还是雷到我了,当然,她真的要生也未尝不可。
平常,我也去跟吊车,偶尔也会去杭州、上海跑长途,和曹薇隔得远了,自然很想念。卸货之后,我到处找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爸妈在家,也不好说啥,她只有捂着听筒,听我说疯话,在那儿咕咕地傻笑。
一到了晚上,北京的郊外有些凉,虽说寸土寸金,首都城市的绿化工作真的不错,就算雾霾严重,但一点也不影响市民的平均寿命。
一架夜机从头上飞过,沙窝离首都机场不远,飞机的轰鸣吵醒了思绪。是的,我现在才明白,我有多么地向往和曹薇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平平淡淡,分开了,却是撕心裂肺地挂牵。而当时,我总是要背道而驰。或许,年轻真好吧!
第二年的春天,南坝河两岸开始绿了。这个季节,曹薇怀孕了,妊娠反应特别强烈,到了吃啥吐啥的地步。这对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
当一切顺其自然到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人总是要结婚生子,和相爱的人白头偕老。如此,我便坦然了,也自然告诉了家里。
然而,事实和愿望很难重叠在一起。一周之后,我接到电话,家里的工作落实了,要及时回去报到。的确,我思考了一分钟,坚决回答,我不回去。
我要跟曹薇在一起。
曹薇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是我遇见过最没有心计的女子,除了她不会与我回湘西生活,她顺从我的一切。曹家就这么一个孩子。我忘了说,曹薇的大伯和三叔都夭折了,四爷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他也不想找女人结婚。
我和曹薇有了孩子,四爷自然高兴的不得了。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也正如后来我站在紫草坞地铁口,不知何去何从一般。来又如何,去又怎样?
最后悔莫过于我将家里的事告诉了曹薇,其实我想带她回去,结婚工作两不误。而在当时,北京跟湘西的距离很远,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但凡一个姑娘嫁过去,也跟没养这个娃差不多。
过去好多年我才整明白,每个时代人们的想法都不尽相同,如果当时的经历发生在现在,我与曹薇之间的距离真的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回不去从前。时间加持不了肉身,肉身驾驭不了灵魂。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凡人。
一个男人,更多的是在做自己,不会为谁而改变。一个女人,更多的是为了一个男人去改变自己。嗯,当然,我只是指我的青铜时代。
曹薇抚摸我消瘦的脸颊,就像抚摸一个可怜的小孩,她带给我的感觉很舒服、很受用。
然而,此刻我觉得恍若隔世。其间,我们究竟是怎样一别就是二十多年,我对这个过程百思不得其解,这可能就是命,刻在骨子里的命运使然,谁也不能改变。
世间万般事,诸般皆随缘,人和人之间原本没有什么对与错。离开北京,天空是蔚蓝的,再次来到北京,天空有些抑郁。南坝河,与往日不同,淤泥清理得干干净净。然而,心情却不可同日而语。
曹薇与我在一起的时光不长,还没超过两年,却像是了解我一辈子。她说,你就回去一趟吧!我也想跟你去,就是反应太大,身体吃不消。曹薇的父亲原本坚持要她跟我回湘西一趟,两边盖一个公章,把结婚证领了,看女儿病恹恹的,也不好再发表自己的意见。
倒是四爷对我依依不舍,他拉着我的衣袖,厚儿啊,一定要回来啊!你不来,我这个院子空落落的哩!
回去的前一天,我喝得酩酊大醉。
这是小刺猬交配的季节,黄沙从盐碱地卷起,似乎都吹进了口齿,不干不净,但也不难受,丝毫不影响我们唱《喀秋莎》《橄榄树》,唱《外面的世界》《北方的狼》……一直唱到月亮落西山。我心疼曹薇,于是提出要回去。我发现,黄三也恋爱了,他搂着凤凰的一个女孩儿,这是他后来的妻,温柔娴淑。
第二天,曹薇告诉我,明权出事了,大腿被钢板扎成两截,他的老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明权我很熟悉,偶尔我们也会相互串门,他的未婚妻是黄三那个村里的,挺着一大肚子,眼看要生了,他是黄三二哥爱人的弟弟,总之一大串,理不清剪还乱的关系。这让我心惊肉跳。
曹薇送我到北京站,北京站在东城区毛家湾胡同甲13号,直到1996年建成西客站,我再没去过北京站,北京站似乎成了我与曹薇还有肚子里毛毛永别的地方。是的,我是一个小地方来到京城暂时生活的乡下孩子,后来我也走过很多地方,却再也找不到像沙窝那样干净的村庄。
回到家,我去了一家国营矿山上了班。在办公室我经常和曹薇煲长途电话粥,这是我在矿山唯一感到快乐的事。不久,我在矿洞例行安全检查,眼看洞壁掉下来的矿石块就要砸中办公室的李小沫,我将她往旁边一推,之后,我只记得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安全帽滴溜溜地滚到一边,然后我人事不省,在医院躺了三年……
我能想象曹薇在我失去联系后焦虑的心情,而当时,我真的想不起关于过去的一切,记忆力丧失,对我来说是一种切肤之痛。实际上,我能感觉我的身边除了李小沫之外,还有其他女人来过,我问李小沫,她红着眼,什么也没说。
生活就像过电影,无数桥段闪现,而我已经无法赘述。
二十五岁的时候,我结束了单身生活,和李小沫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我和李小沫从政务中心走出来,解除了法律赋予我们的关系。我离开了我和她生活了二十年的家,她告诉我曹薇曾来过湘西看我,大着肚子,挺美的女子。李小沫欺骗了曹薇,说她也有了我的孩子,请求曹薇把我让给她。“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李小沫静静地看着我。
我想起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在任何一个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直角边的平方之和一定等于斜边的平方。但是,这条定理用到人们的感情生活中,却一无是处,大概是我并没有完全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吧。
正要离开紫草坞时,我分明看见一辆轿车从身边驶过,第二排是四爷,没错,他烧成灰的样子我都认识。开车的是个女司机,坚毅的脸庞,依稀是曹薇。副驾是个男孩子,戴着眼镜,很斯文。那孩子是谁,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视力出现了问题,或是我害怕知道这个结果。
离开北京,天空依然蔚蓝,从八千多米的高空俯瞰地面,北京城有些模糊,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分不清哪里是沙窝哪里是我……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认瓜记
下一篇:散文 | 物理探究,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