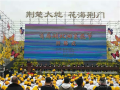父亲的婚姻
珺羽
今天是我父亲大喜的日子。
此刻,我与他站在长桌的一角,我手里叠着装饰用的玫瑰,他在摆放着食物的盘子。我们之间很沉默,与庭院里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我们都有心事。
阿姨们递给我新的红布。玫瑰是用来挂在树上的,冬天后院里的老树落得只剩枝干了,看起来比较萧条。“结婚就该喜庆点”,老人们这样说,于是门上贴了红双喜,房梁挂了红灯笼,院落里整齐的摆了八排长桌,桌上都铺了上好的大红色绸布,绸布上放着煙酒、榚点、水果、煮好的鱼和挂红的猪头。
“我们去把这些挂上,你先叠着。”阿姨们从地上捧起叠好的花,装在篮子里,很快长桌就只剩下我与父亲两个人。
沉默已持续了一上午,父亲只说了句“我今天结婚”,具体也没跟我说是谁,不过这么久我也看明白了,我以后的母亲,就是现在院里张罗着的那个叫他哥哥的人,就是这点,我特别想不明白。
“你想清楚了吗。”我开口了。
“嗯。”他点了下头。
“她是你亲妹妹。”
“大家都知道这点。”
“那以后孩子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近亲结婚,孩子不是残的就是傻的。
“……”他沉默了一下,“这个不担心。”
“怎么说?”
“……”
“哇——!”几个小孩扑了过来,打闹的声音盖过了他说的话,我没能听清,我皱着眉头训斥他们,他们对我做了个鬼脸,抢了我几朵叠好的玫瑰花,拿走几张红布,便去追旺财玩了。
“我不是你奶奶生的,”父亲突然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我一下子愣住了,“我是你奶奶从外地捡来的,和她原来儿子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人。”
沉默,事情变得乱七八糟了起来,这话我是笫一次听说。我的父亲不是会开这种玩笑的人。我还想再问,但是他向我摆了摆手,不愿再说了。
婚礼如期举行,我坐在人群里,看着父亲和他的妹妹拜天地,他们穿着大红色的礼服,手捧红袖球,司仪叫着:“请喝交杯酒。”长桌上的人们都站了起来,手捧酒杯,为他们庆贺。
“沐沐,”同桌的阿姨叫我,“酒快没了,你去厨房催催,让他们再抱些过来。”
“好。”
我穿过人群,逐渐远离了身后的热闹。厨房的门不知为何是关上的,里面有炒菜的声音,还有人在聊天,我抬手。
“老李这一生啊……该说是可怜还是可喜呢。”在说父亲?我的手停在空中。
“老婆子去世那晚啥都说了,你知道老李是怎么来的吗?”
“怎么?是偷生的野种?”我拽紧了拳头。
“不是什么野种,不过的确是“偷”来的。”
“听说是出游的时候遇见的,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呢!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那时候小子得病,不是得换肾吗,哪知道天要助人,跑到南边海城去办事,看见一个一模一样的孩子在路边睡着了,李家人守在那里一天,都没人来领,问孩子也说不清楚父母在哪。他们就带着孩子,坐车回了家,结果天意弄人。”
“快说吧别卖关子了!”
“就是为了小子的肾才捡回孩子的,结果跑去医院一查,嘿!肾根本没法用,你说两人模样都是一样一样的,怎么那器官就对不上呢。”
“后来没法,李家人不能把孩子送回去,也不知送给谁,只得把这孩子关在柴屋里,躲躲藏藏就是一两年。”
“后来小子没找到能换的肾死了,李家人把捡来的孩子当自己儿子养,那就是老李。”
“听说老李与他的妻子关系很好?可好人命不长,竟得病死了,老李还伤了很久的心。” “就是,老李命苦啊!”
“听说老李现在这女人是生不出孩子,被男方给离了?”
“是啊!这样的女人这辈子哪还有人娶啊,这不,老婆子还有一口气的时候,非逼老李跪着发誓娶她女儿,不然死不瞑目呢。”
“哎……老李噢……”
门内的人们接连叹着气,我在门外哭成了泪人。
人生真的如此怪异吗,为什么有的人一生自由平坦,而有的人生来就被命运囚禁。人为什么非要降灾难于他人呢,如果神抽走人类灵魂里的自私,大家是不是就能过得好一点了呢?
一个月后,我问我的父亲,你恨奶奶吗?他久久的看着我,然后叹了口气。
“恨,从前恨,直到遇见你母亲;后来也恨,直到遇见你,就原谅了她。”
我想命运要囚禁一个人太容易了,只要在无尽的痛苦里丢几颗糖,我原以为囚禁我父亲的是奶奶,没想到我也在囚禁他。
人生啊,为什么很容易就让人卷入一些怪圈呢。
詹珺羽,女,德阳人,1997年3月生,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理事,曾在《青年作家》《西南文学》《成都故事》《金银滩》等发表小说散文多篇;有作品入选《四川省散文作家自选集》《当代文摘作家精品文集》等。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散文 | 我读王维《终南别业》诗
下一篇:癌症与无助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