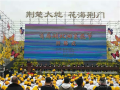南市街印象
文 /刘佳富

南市街在浏阳河南岸,天马山麓西侧。街头曾经有所小学,我启蒙的地方,也是母校,当时的班主任李老师和吕老师如今仍健在。我还记得那时妈妈带我去报名入学,李老师要我从1数到100,结果数到80几的时候又回到了60几,颠三倒四数了几次,才勉勉强强报了名。想现在的小孩子都鬼精一样,天天家长陪着这个培训班那样辅导课,跟我们这些小时候只晓得玩泥巴的“七十年代生人”相比,简直就是幸福飞上了天。

南市街不长,也就两百多米吧,两边都是低矮的民房,街心是麻石板路。当头有个黎剃头,手艺好,擅长修面,一把剃刀在吊在椅背后的皮带上“刷刷刷”几下,手起刀落,脸、脖甚至后背心的寒毛纷纷扬扬飘落,手一摸皮肤,光洁清爽,让人容貌一新。

街中间巷子那里有口吊井,大约七八米深,水质清澈,周边也是四四方方的麻石。人站在井边,用吊绳将水桶往井下一扔,晃动两下,桶口入水下沉,当浸满一桶水后猛地往上一带,一桶沁凉的井水就提上来了。老街的居民就用井水洗菜,用洗衣棒在麻石上捶衣,给小孩子洗澡。大热天把西瓜泡在井水里,傍晚劈开,比现在放在冰箱里的西瓜还冰。

记忆最深的是南市街两边一线的菜摊子,当时觉得这里的菜挺新鲜,而且“烂屎便宜”。当时还没有城管,也没人来收摊位费、垃圾费,前来卖菜的是荷花坊、唐家洲、牛石岭等一带的菜农。那时浏阳县城的早市除了南门口、西门口、城东、北岭外,就数南市街最热闹。因为周边有酒厂、麻纺厂、木工厂、包装厂、粉酱厂等企业,职工人数众多,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肉菜,基本上就是到南市街来解决。或许生意过于兴隆,就像湓溢的水,生意自然就淌到街尾角落来了。还有浦梓港、城西旅社甚至氮肥厂那边的爹爹娭毑也因图便宜跑到这边来买菜了。

那时卖菜没设固定摊位,甚至没有地摊布,就是一担竹箕、箩筐甚至竹篮子略微齐整地摆在街边,菜搁在里面随选任挑。菜农一杆星子秤,绝不少斤缺两,一般称秤时秤尾都翘得老高,惹得顾客喜笑颜开。有的菜农图利索,就一堆堆一把把的卖,而且卖得速度也快,一般上午卖完回去还可以下地干活。当然也有滞销货,到了中午还没卖完,有人就支起个塑料棚子。正午当时,南市街也没了几个顾客,菜农就把菜堆到一边,躺在竹椅打起了呼噜。脚下是腐烂的菜叶,蝇子在嗡嗡飞舞。有时候也看见有小孩,在父母卖肉案板的角落里,旁若无人的咬着笔头,写着作业。
记得那时家里栽了很多四季葱,我和姐姐、弟弟提着竹篮子,用稻草把葱捆成一把把,学校放假时就到南市街来个卖葱比赛。通常是一毛钱一把葱,我发现了个秘诀,就是在卖水豆腐的摊担边最好卖,所以好几次我都比他们“得胜归巢”快,而我得到的最大奖赏就是利用卖葱的钱买了本《新华字典》。可惜这本我的启蒙书,后来不知抛到爪哇国还是扔进历史的故纸堆去了。
冬天酷寒,夏天闷热。南市街低矮的房子,屋檐贴着屋檐,老街坊的柴米油盐、嬉笑怒骂和鸡零狗碎,都随着看似杂沓却无比温暖的人间烟火气,沉淀在浏阳河酒厂时刻缭绕的酒糟芬香里。经历了风霜雨雪,岁月轮回,城市发展了,南市街,我的母校,还有那个下午3:45准时锅炉鸣笛的浏阳酒厂都拆掉了,南市街产的“浏河炸”也成了一代老浏阳人的记忆。
南市街整体拆迁开发后,建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商品楼小区,我本人一家现在就蛰居于此。菜市场搬到了巴山坳,后来又不知什么原因搬到农机公司后面。搬来搬去,生意似乎没那么红火,人气也没那么旺盛了。或许现在的年轻人更习惯去便利店或超市买菜购物,更有电子网购、蔬菜配送和跑腿公司直接把新鲜菜品送到家里来,但我总觉得还是要到菜市场去体验城市的烟火气“润味”些。尽管总有保洁员拿着扫帚在我们脚下玩着“流星锤”,总有剖黄鳝的小贩将面前的脚盆搞得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总有一堆堆零落的菜叶,但菜市场永远都是一个充满生活仪式感、杂乱而又生机蓬勃的地方,耳边有吆喝叫卖、讨价还价甚至骂街的声音,这样原汁原味的庸常,时刻提醒我们人生应保有最朴素的本质,科技如何奔跑,都挥不去生命最初的原点。
这些天,四处的地摊摆起来了,像菜市场一样,生活的艰辛、不易和确幸,都在最接地气的人来人往之间,接通着城市与生活之间最淡定的呼吸 ......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王鹏:胸怀大爱 笔著华章
下一篇:湖南新田:笑迎八方客 彰显税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