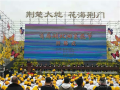父亲的菜园子
文 刘佳富
在荷花观音庙那边“开发”了一个小菜园子,离家有七八里路吧,隔三四天就拖着小车子去施肥、浇水、扯草、松土,一番劳作后带回一把把鲜嫩的菜蔬,让全家上下尝到了真正无公害的绿色食品。
小时候,家里在浏阳河畔的唐家洲上有个很大的菜园子,父亲一年四季在园子里挖土锄草,轮着季节精耕细作,除了自家吃的,这园子里一茬又一茬的蔬菜瓜果,最后都要在一个又一个滴翠的清晨,运到南市街、西门口,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开春时节,父亲就开始忙碌起来,除草,翻土,砍树枝,买种子肥料,安排一年的栽种计划,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白菜秧、丝瓜秧、南瓜秧、黄瓜秧等就在一排排冒着“汗”的塑料棚子里破土发芽。秧苗涨到10多厘米要进行移栽。我抡起小锄头,在沙土上挖下一排排浅坑,小心翼翼地为那些秧苗培土,压实,扶正,淋上几瓢已经“勾兑稀释”的尿水,这些苗子便采天地营养,吸阳光雨露,开始一天天疯长。遇上天气干旱,大人们免不了为长势正好却被晒蔫了的秧苗着急。放了学,我们就帮父亲到浏阳河里挑水,一瓢瓢地浇下去,那些耷拉着的叶子立马焕发生机,经过一个晚上的呼吸和滋养,又活泼泼的绿油油一片。
父亲种得最多的是豆角、黄瓜和凉薯,这些蔬菜产量大,销路好,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打篱笆。好在父亲早有安排,还在头年冬天烤火的时候,枞树桠、杉木条、竹枝、细蔑,就一捆一捆地准备好了。那时家里有根很长的铁棍,专门在沙土里面“打眼”,然后把这些枝桠插进去,顺手将小苗的触须绕上来,它们就像牵牛花一样欢快地顺着往上爬,用不了多久就会开出花骨朵儿,引来一群群的蜜蜂,还有漂亮的花蝴蝶。而我们就围着菜园子跑啊转啊,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最早上市的应该是空心菜,浏阳人都叫藤菜(土话叫“甜菜”)。读初中的时候,地理书上说东北盛产甜菜,可榨糖。我很奇怪,这叶子菜怎么能榨糖呢,一点都不甜啊。后来才知此藤菜不是彼甜菜,我们浏阳人叫的藤菜,长沙人唤作蕹菜,开白色喇叭状花,其梗中心是空的,所以它的学名“空心菜”很形象。乍暖还寒的时候,从棚子里面采摘的空心菜最是抢手,也能卖个好价钱,大抵经过一个冬日,人们腊鱼腊肉吃腻了,这嫩嫩的叶子菜最爽口甜润。到了热天,还有一种“真甜菜”也很畅销,茎长节多,切段和豆豉辣椒在锅里一顿爆炒,最好滴几点醋,酸酸的滑滑的,非常爽口。
最难“侍候”的当属凉薯。说它难,主要是“工序”难,费时又费力。当凉薯苗子沿着篱笆长到齐人肩的时候,它的主藤上会长出很多蘖枝,这时必须把这些蘖枝摘除,不然过几天这些蘖枝就会“张牙舞爪”,长得茂盛异常。而它本身的叶子却渐渐枯萎,吸取不到足够的阳光,加之营养成分都耗费在蘖枝上去了,可食的根茎就发育不全,长得非常小而且硬,根本不能上市。所以隔三差五就要去摘蘖枝,那个流出的汁液又有轻微毒,茎杆上毛茸茸的,皮肤沾上去又痒又痛;加之天气又热,人钻在凉薯地里,保准大汗淋漓,比什么减肥运动都有效。
印象最深的是栽葱。家里的葱主要分四季葱和火葱。顾名思义,火葱在热天长势旺,个头壮,但怕缺水,因此每天浇水是必修功课。四季葱倒没有那么娇嫩,耐得干旱严寒,香气也更浓烈。记得小时候感冒了或着了寒,母亲扯一把四季葱,切成段,放进锅里和豆豉一起煮,那鲜香味飘得老远,而我一喝,浑身热辣出汗,寒气也跑得无影无踪。家里四季葱栽得多了,我和姐姐、弟弟提着竹篮子,用稻草把葱捆成一把把,放假时到菜市场来个卖葱比赛。通常是一毛钱一把葱,我发现了个秘诀,就是在卖水豆腐的摊担边最好卖,所以好几次我都比他们“得胜归巢”快,而我得到的最大奖赏就是利用卖葱的钱买了本最新的《新华字典》。
后来,城市发展了,河边上那块菜地被征收,开发成临水而居的楼盘。父母也随我住进了小区,从每个清早荷锄而耕的菜农,变成了每天要上街买菜的居民。父亲买菜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很早出去慢悠悠地四处看看,过去他们习惯了的南市街早已变了样,搬迁后的那一个市场,却够他们来来回回踱上两个小时。往往妈妈打电话等着他篮子里的包子、米粉,他却还和昔日种菜的老伙计一起,在烟酒铺子里喝着小酒。
舍不得离开菜市场的父亲,内心深处是否还眷恋着那让他年复一年累弯了腰的菜园。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散文│平常心让我又赢棋
下一篇: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