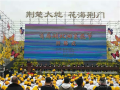父亲的老屋终于拆了,在今年的五月。
其实,做拆老屋的这个决定,我犹豫了很久。不仅仅是因为有阻力,更重要的是舍不得!
及至到现在,老父还在念叨“都怪今几啊,我的老物什不见了”。我又何偿舍得这老屋的一砖一瓦,一什一物……那是我的父辈、我的童年以及青少年时代的全部记忆。
然而,老屋实在是太过破旧,在四面洋气的别墅群中,犹为醒目。况且政府把它定为了D级危房!拆旧立新,势在必行。
于是,请了几天的假,风尘仆仆的赶往故乡。
父亲的老屋很有些年头,大约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墙的主体,一半是红砖,一半是土砖。这些红砖、土砖全部是我们一家五口自制而成。那时,没有机器制砖。父母从近旁的河里淘来河沙,挖了粘质的泥土,用木桶挑水,用锹把这些搅拌成泥团。泥团需不软不硬,恰到火候。制砖的活儿是姐姐的,站在一个半人高的土炕里,姐姐总是把这些泥块精准的砸进砖盒,然后用线一拉,取掉砖盒上多余的泥土,松开砖盒子,一块砖坯初具模型。再在码砖坯的长条木板上撒上干燥的沙子,接着把砖坯整齐的摆放在木板上。
搬运这些砖坯,则是我和妹妹的活儿。这自然是所有活儿中最轻松的了。我和妹妹每人每趟搬六块到十块砖不等,送到大约一百米处。这里地势稍高而平整,父亲再把这些砖坯码成一堵堵整齐的墙,以便风干。一天几十百趟下来,我俩都累得浑身散了架,稚嫩的小手早己粗糙不堪。
那时我俩都是不到十岁的孩童!但想到有新房住,我们还是充满了干劲。
制成这些砖,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晒着的这些砖坯得随时提防风和雨。风太大,有可能把这些等待风干的砖墙吹倒;不期而至的雨往往让在田地里劳作的父母惶急的赶回来给这些宝贝砖坯盖上稻草。包括后面的装窑,点火……每一步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
经过前期几个月艰辛的准备后,终于开始动土了。
父亲请来了四邻乡亲帮忙!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乡邻们盖房是互助式的。张家盖房时,只要吱声,李家不管有闲没闲都得帮上几天忙,这是不要一分钱工资的。李家盖房时,张家不需邀请,会主动的上前帮忙。
还记得几年前父亲的唠叨“谁家盖房,他出了一个月工,并不要人家一分钱工资,也不曾吃过谁家一顿饭”“谁家的老父老母去世,都是找老父帮忙挖的墓穴”。
有时父亲说多了,我会怼回去几句:“爸,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钱是不会有人来干活的。”听了我的话,父亲总是耷拉着苍老的脑袋,半响不语。
言归正传,在乡邻的互帮下,老屋的主体告成。给屋盖瓦,便成了我脑中不能忘却的风景。
乡邻们把烧好的瓦挑到房子一角,摞成有序的堆,然后在墙上架上木制的梯子。我们这些小孩也混迹在大人堆中,一排排整齐的人梯从瓦堆旁一直延伸到屋顶,每人手里的瓦竟似现在流水线上的工人,整齐而有序的传递着。大家有说有笑,严肃而活泼,仿佛自家的房屋落典而成。鲜见有瓦片从谁的手里意外滑落的。
当然,也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在房屋落成后搞个庆典。所谓庆典无非就是把乡邻们请来,有荤有素,有酒有肉的招待一顿。最有兴头的是,主人家把早己准备好的糖、果、瓜子、糍粑……从屋梁上撒下来,天女撒花般。堂屋里的客人们便欢呼雀跃,有抢到糖的,有抢到瓜子的,有抢到糍粑的,也有空手而归的。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闪现着快乐的光彩。
我家是没有这个实力摆酒的,但进伙时,从来不待见我们的奶奶竟然主动的帮我们点火烧柴。这让父亲和我们有点受宠若惊。要知道,在当时饱受封建思想浸淫的奶奶坚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只生养了我们三个“赔钱货”,受到的冷遇可想而知!
现老屋己拆,新屋己立。关于老屋的一切记忆历久弥新!
那时,家人和睦,同舟共济。乡邻淳朴,互帮互助。这是老屋留给我的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
(注:“今几”是我的小名。原创人:杨金姣。)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中国美术馆脱贫攻坚作品展在京闭幕
下一篇:“中国·湖南永顺莓茶文化节”在芙蓉镇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