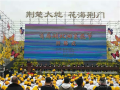今天是父亲节,想起远在天堂的父亲,也许许多人都感同身受:苦日子过完了,父亲却老了;好日子开始了,父亲却走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一生爱酒,醉了也说酒话,甚至对母亲动手动脚,但却有着非凡的谋生手段和宽广的胸襟。
父亲会做多种手艺,除了基本农活,他还会做木工、篾工、泥水工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是贵州省毕节市威宁自治县牛棚片区红极一时的烧瓦师傅。据他自己及周围的老人们说,牛棚区怕有一半以上的瓦房上的瓦都是我父亲烧的。烧瓦的间隙,父亲就利用家里或是邻居家里起房盖屋剩下的边角废料拼做出一些桌椅板凳、锅头甑脑之类的小家具用以出售或者送给亲戚朋友,以此补贴家用或者帮助大家解决一些不时之需。也许正是因为父亲具有这些多样化的谋生手段,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他才能够支撑起一个8口之家的大家庭吃穿用度,甚至培养出了我们弟兄三个国家干部,令周围的人们至今谈起这些事情都是啧啧称奇。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能说会道,心底善良。他常说,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拿给别人;自己都不想听的话,不要拿去骂别人。族中邻里不管哪家与哪家,凡是遇到那些扯皮垃瓜的事,都会请父亲前去“断理”。说也真怪,刚刚还在骂骂咧咧的事情,甚至是大打出手的事情,经过父亲的一番调理,大多能够合好如初。为此,那些年父亲总是经常给人家当红白喜事的总管,在方圆几十里威望极高。
父亲爱酒,但那些年代没有什么好酒,能有点包谷酒就不错。听父亲说,那时候粮食紧缺,国家不准私人办酒厂,粮食必须统购统销(因此我真的很不相信一些小酒厂随便出一款酒就号称三十年陈酿五十年陈酿什么的)。父亲说,他们甚至喝过“青岗子”酒,那酒虽然能解酒瘾,但是喝醉了以后特别口渴,脑壳像打烂掉一样的疼。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甲醇,只是在心里想着,哪一天万一自己“出息了”,一定要给父亲买上几瓶好酒。
后来我考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或者父母来到我们家里居住的时候,我就尽其所能地买“瓶子酒”来与父亲俩人对饮。我们父子两个酒量都不差,一瓶酒都底朝天了,还有点添嘴抹舌的。那些瓶子酒喝多了照样头痛,虽然没有父亲说的老火,但也很难受。然而父亲却淡淡一笑,说比起他们喝的青岗子酒来,已经好得太多了。但为了醉与非醉中间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我们弟兄几个就一直陪父亲喝到了他老人家于2000年去世。
父亲走了,弟兄们甚至是弟兄的子女们都勇闯天涯了,面对现实生活中多姿多彩的酒场战场,我独自应酬,挥酒自如。也许是彝族人天生有点酒量,也许是父亲健在时的教导有方,经年下来,与爱酒人士们大战起码数千回合,终也难分高下胜负。直到2014年的春节期间,因为鏖战时间过长,也因茅酒度数太高,不慎就把我给整胃出血了。在滴酒不沾,面壁思过的那几个月里,我老就在心里想:能不能整出一种价格适中、度数适中、口感又好的白酒来呢?也许是所谓的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吧,后来就有了“天星酒”的一系列故事。
现在,喝了头不痛、口不渴的“天星酒”我是把她发明出来了,但是父亲却过早地走了,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遥祭一杯天星美酒,并写上这段简单的文字,聊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敬爱和祝福吧:愿天堂真的没有病痛,愿天堂里的父亲母亲永远快乐,幸福安康!(禄炳宪)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上海闵行:市民舞蹈登上剧院大舞台
下一篇:散文/反面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