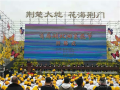梦回老宅
湖南攸县作家协会 李放鸣
“家是无法选择的摇篮,
家是世上最美的港湾,
家是心灵窒息的牢笼,
家是柳暗花明的世界。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散了未必再聚,
聚了终究还要散。
噢,家是什么,是什么?
噢,家在哪里,在哪里?
家是不可割断的血脉相连,
家是难以摧毁的永久记忆………”

故乡之春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当你一进了攸县坪阳庙乡黄公村炉下冲,就会看到有一大片屋连屋、户连户的矮土屋群,且它们以祖上公屋大厅为中心划分为“耳”字形状。我家老宅就居于它前面的西南部位,这里不仅位置中心,南面空旷,整个山冲一览无余,而且占地面积大:从前面看,有祖父住的灶屋、拐子屋、睡房、地楼间、一排四间;若从西面看,有牛栏、厂下屋、住房、上厅屋和厕所,一长溜共五间。自家的鱼塘、菜园和石坪,呈半月形从西边绕到南边,还砌着一道矮墙与外隔离。这些房子,皆有楼,窗户小,滴水低,大概只有1.2丈高左右,是田泥土砖砌的墙,短青瓦盖顶,不知是建于清朝还是民国。
我家老宅以祖上公屋大门为门,从祖公屋下厅屋右边的一条又黑又结实的侧门进入,便来到了我家的第一间房子——厨房。那时,这厨房被祖父和父亲临时用篾塔从屋子中间隔成两半,上边是父亲的厨房,在紧靠上边墙壁处用土砖砌成一个大灶堂,用来煮猪食;砌一个中灶堂,用来烧水洗澡;砌一个小灶堂,用来炒菜。土灶呈半月形状。灶门用两竖一横的大青砖砌成,灶体全是土砖。灶面用“三砂”反复揉平,使其牢固美观。灶门上还从山上特别采伐有节钩的硬木做成“索钩”,在索钩上各挂着一个铁鼎罐。灶后,挨墙横搭一块“案板”,盛放各种餐具和灶具。灶前是一个长约灶长、宽为2尺的“灰坑”。小时候,我家有一块又长又宽又厚又硬的矮凳,横放在灰坑前,人朝灶门烧火,身后便是一捆一捆的干柴,而这条长凳又成了一道自然的防火安全线。越过“厂”型篾塔,便是祖父母的灶屋,其灶体形状与布局,大体与父母的相仿,只是他俩没养猪,体积比较小巧。开餐时,每当祖父母有什么“川菜”,总不忘特意为我送来一碗或半碗。灶屋墙壁,天长月久被烟火薰得很黑,楼上还结着厚厚的“堂墨”。灶屋房子大,显得比较空荡,但只在东下角开了一个不大的旧式窗户。每逢晴朗的早上,东升的太阳便在恩怀叔的屋顶上探过脸来,透过黑色的窗格,将明媚的阳光照进灶屋。我还记得满10岁时的那天早上,我在灶屋的旧窗下玩着太阳光,一边兴高采烈地对母亲说:“艾家,我今天10岁了!”又一边尽情地沉浸在这银辉色的太阳光线里,手舞脚蹈地欢快跳跃,显现无限的生命活力,自我观看,自我欣赏阳光映照在地面上的各种身影,妈妈脸上荡漾着妩媚的笑容。

梦回老宅
在灶屋东南角的下方,开着一条小门,便来到了祖父母平时的坐屋。坐屋铺有黑色的楼板,楼下的上方墙边放着一个四层的、古老的长方形谷仓;南墙上有一个木窗,窗下放着一张小桌和许多凳子,是吃饭的地方。此间窗子虽古老窄小,临窗远眺,视线开阔,家外有事,一瞧便知。
继而从西南角上入门,便进入了下拐子屋。下拐子屋三面临墙,上边是天井,比其他房子要窄小得多,长约1丈,宽仅7尺,它的主要作用是过路,在其西南角仅放一个竹木制成的方箱式小鸡埘。平时,鸡鸭混放。若有家禽下蛋,祖父母就弯一个有长柄的竹圈,伸到埘里去勾蛋。1960年正月,祖父被一恶人打残后,嘴歪向一边,口里常咳着又黄又臭的浓痰,用一个小小的圆铁皮桶子盛着,常叫我到小塘里去清洗。他坐在这拐子屋里临时搬来的小桌边,靠一只小焙笼盛火取暖,回英奶奶就陪伴在身边,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往下拐子屋西进一条侧门,是一间一丈见方大小的祖父母住房,南面墙壁正中开着一扇小窗,临窗置一书桌,西南墙角是一张杉木旧床,东南角放着米柜,我至今还珍藏着奶奶平时量米的、上面写着“正升”的竹质发红的升子。我还记得,1959年冬下,祖父因饥饿在大园“偷菜”,被凶神恶煞的吴某.黄某强解到大队批斗,父母和奶奶一起,就在这间屋子里,缠着尚坐在床沿边还没离去的李某,请他在吴、黄面前为祖父说点情。此时,李为大队团干部,年青温和,似乎从心里同情祖父的遭遇。
对着祖父住房床后,登五层板梯,便进入地楼屋。地楼屋约1丈见方,楼用木板榨得严严实实,楼下是柴屋(后来生产队关牛),楼上是住房,南是一个小窗。地楼里,盛着祖父的一只精制的香樟材质的小方箱,箱的盖板和扣板,均有雕刻的兰花板画,箱的中层是只推拉的大屉子,下层是两只推拉的小屉子,祖父平时用来收藏账目。可惜1974年建房时,我没有把它当作亲情来珍惜保存,留下后悔不绝的遗憾。
绕出祖父住房,又来到下厅屋。下厅屋有1.2丈宽,连天井有1.7丈长,比其他房子显得宽广、明亮。楼料皆为木匠四方走线的“方尺料”,呈黑色;楼板尽由宽厚的松木板,以“公婆刷槽”合成。厅壁,用白色的石灰粉刷成,在长期的烟火薰熬中,被渐渐演变成了灰黑色。下厅屋的摆设是:西墙正面放着一个古老的神柜,神柜上边挂了许多黑底金字木匾;北墙下有一条长凳,凳前是张小饭桌,还有一副石磨;南墙下对着厂下屋西南角上的侧门,依次放着一张呈红色的竹床和一张同样红色的竹睡椅。夏天来了,这里南风浩浩,凉爽极了。那时,祖父常坐在这睡椅上,将右脚脚弯附在左腿的膝盖上,再用右脚脚尖刁起我的幼小身子,两手牵着我的双手,哈哈大笑地、一上一下地反复打着“叽叽咕咕”。当时,我还有一个是从外面抱来的“黄花女”生的小妹妹,叫“河姑仔”,妈妈常在这屋里为她喂奶。可惜,没过多久就被夭折了,埋在开山冲里。在这屋上边的墙面上,也给我留下了永志不忘的记忆:尚未入学时,当我第一次在黄公庙看了一部“延安保卫战”的电影激动不已,于是我找了许多白石灰颗粒,在这黑灰色的墙面画上了一条条“之”字形的向上道路,斜线上点满了密密麻麻的白点,表示是解放军举旗飞驰打敌人;“发蒙”时,初学了几个阿拉伯数字,便又胡乱地“1、2、3……”地在这墙壁上画了一大块;上学后,“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半墙的奖状,给这个日渐破落的家庭,似乎带来了一丝丝“枯木逢春”的求生信息;1965年的春社日里,奶奶和母亲共同摇动厅角的这副石磨,特别要磨米粉做水饺吃,说是:“社日吃了子﹙蛋﹚,榔头打不死;社日吃了饺,石头踩发笑;社日吃了醒,一生没有病。”这时,我兴致高高地告诉奶奶和母亲说:“我六册语文书上有首石磨谜语说得更好‘千里迢迢在眼前,石头重重不是山,雷声轰轰不下雨,雪花纷纷不觉寒。’”她俩听了笑着说:“这谜真好,只有读书才晓得。所以,你要努力读书,今后才能有出息”;“文革”初期,在这块墙面的右上角,出现了一块光华叔写的约60×90cm大的、白底黑字“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的正楷毛主席语录;“九大”召开前夕,这块墙面上又被贴上了“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畅游长江”“毛主席在北戴河”“毛主席重上井岗山”等6幅毛泽东彩照……

老家遗物
1956年农历12月14日,天气阴沉。那天为了给大弟过“三朝”和父亲30岁生日,家里请来许多客,舅母、月仔姑娘带着兰英、祖英两个姐姐来了,是这间下厅屋唯一一次留给我家中热烈、隆重的喜庆场面。那时,外婆、祖父母、兰英姐、月仔姑姑均在世,且是一次亲情的大融合。
下厅屋上边的那口天井,夹在上下拐子屋中间,四周全用老式青砖砌成。天井长约6尺,宽约不到4尺,深约2.5尺。平时,家里的各种生活垃圾都往里抛。天下大雨时,因井内被垃圾占去了大半空间,地下水道又受阻不畅,雨水一下子满边,往下厅屋漫。这时,家人就要手忙脚乱地用提桶在天井里提水防漫。天井还是一个天然的时间表,那时,农村没有手表和闹钟,父母每天需到地里劳动,母亲就吩咐我:“当日头光线到了离天井约5尺时,就要生火煮饭”。光线到天井时,已是中午,父母正好从地里劳动回来,炒菜吃中饭了。
自大食堂解散至1974年秋老宅被拆时止,与下拐子屋相对应的上拐子屋的那个鸡埘,在这异常艰难时期,是我父母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通过饲养鸡鸭来让它们产蛋,当凑到5个、10个时,拿到坪阳场上去卖,换回这小钱来维持我家的盐油和笔墨、纸张供我上学,平时也舍不得吃。即使到了过节,父亲也是只用1—2个蛋,将它们敲烂,用热锅汤成纸厚的“冲皮”“扩”着吃。
西进上拐子屋小门,是我和父母住的两间睡房。进门第一间没有窗户,只能靠此间两条贯穿的小门来采光。因又处内屋,光线极弱。这间内房只有1丈长,7尺宽。进门右侧,只放了一个用木方架起来的简陋小床;南墙下排放着母亲出嫁的两个书笼子。内房1丈见方,四面墙壁被粉成了桃红色。西窗下有一张红色的小书桌;北墙边放着两个一排的红色什柜,靠窗的一只为深红,靠里的一只为淡红。因为两个什柜,宽均为5尺,并排一放,屋内的纵向空间就基本没有了。内屋南墙角放着一只古老的旧木床,父母亲和孩子们就睡在这床上。床后,是一只盛米的大米瓮。小书桌,早年被漆成红色,由于年代久远,红漆剥落,泛白见木;抽屉里,收藏着各种古铜钱和黄色的小狗“叫吹”,还有精美的铜制酒壶。房的东北角上剩着一个小楼口,楼上堆放着外婆的纺车等各种杂物。小时候,我像猴子样地从什柜的层板上爬到柜顶,又从柜顶攀登到矮楼上,到处翻看家里祖传的那些破旧东西。临窗的小书桌,成了我童年看书写字的好地方。

故乡田园
越过上拐子屋小门,便进入上厅屋。上厅屋有1.1丈宽,2丈多长,三面是墙,一面临天井。天井过后,是一间1丈见方的闲置厂屋,厂屋与祖传公有的老大厅屋相通。上厅屋的布置是:西墙开有窗,屋的西下角是生产队的一粮仓;西上角是我家的一个粜子;正上方是我家的一个四层粮仓;屋正中摆着我家的一张杩木桌子,是我们父子一家的饭桌。
在这长长的上厅屋里,历历往事犹记心房:1958年4月,有位大桥塘陂湾樟树达年龄约5旬,个子不高的奶奶,被家里请来这屋专为母亲治疗眼疾,只见她将母亲倒长在眼内的睫毛,用一只只小小的夹子,小心翼翼地进行精心转翻,一时痛得母亲“哎哟”直哭;1960年遭遇大饥荒,人平整天只有老砰4两米(16两一斤),我被饿得皮包骨头。一天,妈妈非常疼爱地暗中吩咐我:“和爸爸在一起吃饭时,你要大口大口地快吃多吃。”唆我与父争食,还在饭桌下用脚来催我,示意我;1960年,母亲与奶奶在厂里边上靠路的生产队田里的禾秆上捶了约两升半壮的谷籽,晚上全家人就用铁锅炒熟围着吃。过天,母亲胀得怎么也排不出大便,在这生死关头,我按母亲吩咐,用筷尖在祖父厕所为她连续排拨了两天多,才挽回了母亲性命;1962年,赵四外公为我家打了最后的一个粜子。打粜子要找最有粘性的黄泥,还要用米汤搅拌,用双脚将泥踩腻,装于圆形的竹盘里,再用条棰捣油粜油泥,才将事先用油炒好的竹齿,很有讲究地订成排出纹线。那时,为家极度忧心的母亲,常喋喋不休地向父亲唠叨家里许许多多的事情,赵四外公曾见情评论说:“象是‘鬼兆亡’样的口说咯不停。”新粜子打好后,安放在上厅屋,楼上缀根绳子,套上推钩,人推着推钩,使上层旋转,累得人满头大汗;1963年,队里不理睬父亲的百般反对,占去我家上厅屋那头空闲的厂屋,强建了集体的仓库……

老家新貌
从上厅屋北进一小门,便来到我家的卫生间。卫生间东与西六的厨房搭界,北与民祝的晒楼屋共墙,宽有1.1丈,长有1.6丈。屋的西南方位是粪坑,西北角上是一副沉重的石臼,石臼迎面开着窗户。与这卫生间西墙相邻的是祖父母的卫生间,里面只有一个粪池,门就开在外面。
上厅屋以上的三间房子,是父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建的,水料和楼料都是树径12cm的新杉料,屋顶盖的都是新玄皮,房子显得比旧的要宽广,光线明亮得多。因此,1974年建新房子时,父亲强烈反对我拆除他建的这三间房子。后来,他拗不过我,就流着眼泪极其动情地对我说:“你参加了工作,你做得用,不把爹娘放在眼里。”我当时很不理解地回答说:“拆旧建新还不好吗?”啊,我当时未能领悟到:原来是我无情地摧毁了他心目中一生唯一做的伟大事业!
从厂下屋里出来,便来到了我家弯月状的内园,内园的外边,上是祖父的鱼塘,下是炎云的鱼塘,两塘接口处用茅柴挡着与西面大路隔断;上边,与兵生菜园接界,也是用茅柴阻隔不通;下边,一道矮围墙特意与墙外大路隔断,成为一个封闭式的大园子。园子里,最上边的是我家占地约40平方米的仔塘。1965年上半年被生产队用草皮、泥土将其填平,放水干塘时,塘中那在浅水中蠕动的很多红红的鲫鱼,还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塘边有棵古老的楮树,树高约6米,树冠3米,树径约18厘米,叶儿厚实、笔挺,不见落叶;树杆坚硬,树皮为银灰色。它象一位历经数百年苍桑的老人,风雨无阻,又默默无闻地守护着我家的这片家园。1981年,邻人建房时,将他家拆的砖头、瓦砾全部填进祖父的鱼塘里,使这棵老楮树“窒息而死”。夹在上、下两块菜地中间的是个约40平方米的小石坪,是用石灰、沙子、泥土混合为“三砂”筑成的晒谷坪。那时母鸡常带着小鸡在这个坪里觅食。突然,盘旋在空中的老鹰象战机一样地俯冲下来,疾快地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搭起一只小鸡飞走了,母鸡一约而同地伸着长脖“咯咯”大叫,其余小鸡都很快地畏缩在母鸡的腹下避难。当人们从屋里出来驱赶老鹰时,老鹰已远远地飞到了牛形冲四株达20多米高,需几人合围的古松上而“高枕无忧”了。1974年深秋,也是在这石坪上,我可怜的母亲在晒薯丝时,不小心被烂篾塔重重地刺坏了右边的眼睛……
嗅千年馨香,扶百年老床,寂寞的旧衣陈物,挥不去昔日苍凉;那久远的日头,是否也这般明亮?远去的鸡鸣犬吠,幽幽虫声,是否还在这里回荡?一步一回想,那深深的相思惆怅,插在我回来的路上!
梦中,
老宅的影像微微颤动;
遥远的记忆,
伴随清风,
游向那无尽的天边,
倾诉着难忘的情愫。
年轮一圈一圈地隐隐长着,
于这岁月蹉跎中渐渐老了容颜。
于今,
这老宅早已没了踪影,
外婆、爷爷、奶奶,
早走了半个世纪;
父亲,母亲,
长眠在远处的青山,
给我留下它深渊一般的逝去岁月,
再也没有一个老人喋喋不休的梦呓……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数字化助力中华传统文化“活”起来
下一篇: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