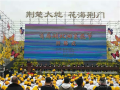奶奶,您在哪里?
李放鸣
不知历史上的哪一个年代,“哗!哗!”的连天大雨下了个天地间日夜不断线,沉沉的乌云和雨雾,弥漫笼罩着山峰、地坡和田野,久久不能散去——在这连绵起伏、横亘在攸醴两县边界的桐岭大山边,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灾!山洪从这气势高高的山峰上,拍打着它两岸的悬崖峭壁,飞溅着白白的浪花,象千里跃进的战马,吼着汽浪,泻下山来。泻得那野生在山壁上的树木根儿露露;泻得那大大小小的山石,“咔咔嚓嚓”地滚下山坡。突然,在这“哗哗”奔瀑的洪水声中,夹着“轰!轰!轰!”的几声巨响,震的山摇地动,震声在这深深的山谷里久久回响。忽地两个巨大的石头,伴随着奔瀑的洪水,一前一后地随即进入了这座高峰下的山冲,又继续地滚了下去。滚着,滚着,滚到了山冲的中腰,不知什么缘故,竟笨立地“窝”在这山冲低洼的江床里,一动也不动了。人们都说,正是因为这里有两只大蛒蛄精,特地叫“上帝”为它搬来,作“家”住的。从此,这两只“蛒蛄精”各居一个“家”,屹立在这山冲的正中,度年过月。因此,人们特地为这个无名山冲,起了一个有“根据”的名字——“蛒蛄冲”。
“蛒蛄冲”是个荒凉空旷的偏僻山冲,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长年累月,也难得见到几个过经的人。绸密的山林,竟相生长在这山冲的上上下下,开花落叶,周而复始;林间,百鸟争鸣,展翅飞翔,搜山巡林。山下各种杂草,四处丛生;山涧,“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上山下,野兽众多,弱肉强食,虎豹扬威控大冲。尽管野兽众多,但难见几名猎手来捕杀它们。千百万年来,这树木封山、杂草遍地的山冲,只不过是一个野生动、植的世界,无人开发,更无人住家……
后来,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进程,到清末民国,人口有了发展,苦难的劳动人民,迫于生计,开始到这个“虎啸狼嚎”、“天高皇帝远”、尚无人问津、山地无主的地方,开始开荒栽树、造田造土。在铁与火的宣战下,它渐渐地换了模样,山冲中出现了一层层梯田,一块块新土,一片片油茶林。于是,它变成了农人希望的地方——春天,山冲中一片片小麦,被春风吹得垂头钩脑地成熟着;夏天,被阳光雨露哺育成长的稻子,由青转黄地结果着;秋天,满坡的油茶,“笑盈盈”地供人采摘;十月间的红薯挖不尽,季季兰草花开,鸟儿“啾啾”闹着山,清凉的溪水涓涓长流……这里一时间,又似乎成了一块“世外桃源”。
时间到了1968年的秋天,我们祖居的炉下上下两垅,人口由解放初期的10多户、40多人,迅速发展到30多户,130多人,并且全部“窝”在家里搞“大集体”。过度开发、消耗、榨取大自然资源。“蛒蛄冲”和下面的矮山一样,山林、地柴也被砍光了,路旁、坡中的“草皮”被锄净了,虎豹早已绝迹。被“文革”鼓燥了三年的人们,决定在蛒蛄冲办一个什么场。由于有大量的劳力,砍的砍竹子,斫的斫冬茅,仅用数天功夫,就选择在沙子坡与同老湖两冲交界的山咀下的一块小坪地,搭起了一间占地约30—40平方米的、由竹子当墙、冬茅盖顶的简易住房。于是,我奶奶——人称“八嫂婆婆”,便成为这山冲中“三皇五帝”到如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居民。

当年住房之地已是一片荒草
当年,我奶奶已50多岁,身体有病,又单身一人,为什么会能享受这一空前的、如此“厚爱”呢?这得从我奶奶王回英的悲惨身世说起。
我奶奶王回英于1910年10月出生在坪阳庙乡坪泉村榴槐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其弟叫王克昌。我奶奶王回英成年后,不知什么时候,嫁入炉下的李宗生,她的丈夫于1956年病逝。那时,由于我祖父李天生与第三个妻子已离婚数年,他们又同住在近在尺咫的炉下湾里,双方都无对象,两人年龄相仿,相貌、性格合意,就开始了“来往”,成为没有办领结婚证而同居的“事实夫妻”。在我的记忆里,他们能互相尊敬、互相体贴、有事商量,一团和气,从没斗嘴,从没扯皮,过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四五年恩爱生活。可惜,好景不长,祖父在1960年春,被恶人打死了,奶奶重又过着单身生活,住在我家下苏屋那厢的几间小房里。至1967年秋,我四弟出生,全家和奶奶共有7个人,却只有一个仅9分底分,不能算作全劳力的父亲一个劳力,在那靠劳动工分吃饭的大集体年代,我家无法吃上最基本的用粮水平,年年欠着队里一大把账。因此,队里根据这种困难情况,特别将一头老黄牛分配给奶奶放养。这头名叫黑古的公牛,平时显得老实巴交,性情温和,谁都可以接近它、抚摸它。可是,有一天下午,我奶奶在沙树岭下一丘名叫“七担” 的稻田里去放养这头黑牛,它一反平日的温顺,却把放养它的恩人——我的奶奶,突然当成一个大仇敌似的看待,居然蹬着两只红红的眼睛,赶着我奶奶狠斗,我奶奶遇此“突然袭击”,一时毫无防备,被它抵斗在田壁上。这时,我奶奶只好一边大声呼救,一边用右手紧紧抵着它的鼻子往上扭来巧力制约它的凶斗。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将它驱走。但是,奶奶虽然脱离了险境,一条腿却被它斗成了“瘸子”。鉴于这种情况,队里为了维护我奶奶的人身安全,只好将养护这头牛的事儿调给别人,而奶奶却每年失去了放牛的60个工分,落得生活没了门路。因此,队里为解决奶奶的生计,就将奶奶安排到蛒蛄冲这间草竹结构的棚子中去“守厂”。于是,奶奶没有任何拒绝,没说半个“不”字,就在我们的帮助下,卷着极为简单的铺盖和日常生活用品,在这极简陋的“家”中居住下来。由于这里特别偏僻,周围数里无一户人家,连鸡啼狗吠声都听不到,只有山中的鸟鸣和地下的蛙声、虫声相闻。好在虎豹早已绝迹,不存在生命威胁;好在“文革”的大破“四旧”,在心头散了神鬼的恐惧;好在冲中的树柴砍完了,才无从前的那种阴森森的害怕感觉……于是,我奶奶就这样命运无情地迫使她离开真正的人住的家,而独身一人到山野的、远离人群的、不是人住的深山,去孤楞楞地、担惊受怕地“生存”。可是,奶奶却能象杨柳那样,无论插在江里、塘边、田埂,它都能成活一般地灵活面对。于是,奶奶在草棚边挖了许多土,适时种了四季都有吃的零星蔬菜;在棚边拦了一小池溪水洗衫洗菜;在涯下挖了一口小水井,以烧茶煮饭……能“适应”这特殊的“新家”,几个月没有回来。那天,我和定英姐特地到蛒蛄冲去看望她,她对我们显得很慈爱,很亲切,并掏出一只锁匙,叫我俩到老屋地楼上为她找一些东西带去。于是,我俩按照奶奶的吩咐,去“地楼”为奶奶找东西。可是,虽仅隔数月,当我俩打开“地楼”门锁进入,短暂数分钟的时间,由于“地楼”下常年关着队里的牛,满屋牛粪臭气往上弥漫,“地楼”几月未开门流通空气,一股令人窒息的霉臭气向我俩袭来,一下子满身随之生上了豆粒般大的,又肿又庠的红胗。
秋去冬来,蛇类要入洞冬眠了。可是,有一条颜色像绿枝绿叶一样色彩的青竹蛇,静悄悄地偷偷爬到奶奶住的草棚里,进而又爬到床的蚊帐上,后来,缩在床下,奶奶一时没有发觉与及时防避。于是,有一天下午,奶奶不幸被它咬上了。而且,青竹蛇是一种与眼镜蛇、五步蛇、百节蛇一样剧毒的恶蛇,它的毒液迅速窜入了奶奶身上的血管,使奶奶光洁的脚腿上顿时生起了一个个圆鼓、通亮、透明的磷片样的大气泡,奶奶呼吸短促,面临着生命危险。后来,奇生外公及时找到一副好蛇药,才在死亡线上挽救了奶奶的生命。

奶奶就曾住在这远处的高山下
从春的花开花落,到夏的酷暑难挨,到晚秋的凉风潇潇,到冬的风刀霜剑,奶奶忍着孤单,忍着寂寞,忍着辛酸,从1969—1970年在这个厂棚里继续苦熬了两年。
1971年上半年,奶奶得的严重的“崩病”(子宫癌),到了晚期,我们不得不将奶奶接回老家,让她重新住在她与祖父原先住的那几间小房里。没有正常的食物营养,没有一分钱的治疗经费,就这样“坐等待毙”地耐着剧痛,被癌症苦苦折磨着,生命陷入了绝望。
大概是1971年的农历5月中旬,恰逢礼拜天,我从攸县二中回家。第二天,是奶奶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大家看到奶奶快不行了,忙差我到双雅冲里的姑母家拿“装尸布”,我冒着火辣辣的太阳,来回跑了20多里崎岖的山路,午后才回到家里。我亲眼看到了易连英(四嫂伯母)等一大群人围在奶奶身边,奶奶就在她住的那间房里的床角又临墙的一个高栮子的便桶上蹲着,大滴大滴的汗珠从她的额头上掉下来,寸长的灰色的象肠子般的东西,一截截地慢慢从她身上丢到便桶里,看得出,她是多么多么的痛苦……不一会儿就断气了。就这样,天底下一个多么可怜、多么值得同情的人,悲惨地离开了人间。
一个星期内,我父亲和炎云叔叔一道,不知是怎么弄来一副棺材装敛,买了许多肉和鳝鱼(那时便宜)、黄瓜、辣椒等,将奶奶埋葬在“十字路”上面的一个山头上。她在坪泉大队的“娘家人”也赶来送葬。
奶奶远去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奶奶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圆圆的脸盘,五官端正,并布局均匀,脸部轮廊线条舒缓,只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女人。的确,她一生尽管无儿无女,坎坷多舛,但她从未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坏事和恶事。她从不和别人争辩什么,也没有什么癖好。

奶奶用过的量米升子
奶奶的许多生活片断,至今还记忆犹新:
夏天来了,她常在我家的下苏屋对着厂下的门口,脱去上身的衫衣,摇着老叶蒲扇纳凉;在厂下屋的阶级下面,折着几枝带青叶的小树枝,用秕谷压在面上,点火烧着浓浓的青烟来驱蚊。冬天来了,我们在奶奶的小灶屋一块烤火、算数、猜谜;我还清楚地记得珍如公在60年代里喜欢在烤火时,拖着长长的、半唱的嗓音念着报纸;1961年姑姑初嫁双雅大队的下江冲,细心的奶奶第一次就数清了从双雅水库进口处到其家里,要过十八座小木桥。
奶奶是仁慈和爱家的。小时候,她和祖父带着我走过她的坪泉大队榴槐冲娘家;1960年过“苦日子”的时候,队干部半夜偷偷在我家“斗伙”,奶奶有两次趁机留着难得的饭菜,偷偷送给睡梦中的我。祖父因所谓的“落后”,常遭到左倾干部黄某、吴某的批斗,奶奶每次都是硬着头皮为他在他俩面前求情;祖父被吴某打残后,是奶奶天天陪伴在祖父身边,为他生火取暖、做饭、煎药。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大概在1961年或是1962年,有一次生产队将一架原是我家(已入社)的横田铁耙,用后丢在我家忘记收回,在那极左年代,奶奶趁机冒险将这架铁耙收藏在灶屋楼上,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永远珍藏、永远纪念的祖父母共同的、唯一的遗物。

奶奶收藏的铁耙
……
时间一晃,数10年过去了。清明节又到了,家乡烟雨濛濛,山头到处开遍了一丛丛美丽的映山红,我和文明弟弟携着幼小的孙女若静,又一次地来到奶奶坟前祭拜。迎面处,高高的彤岭大山上,厚厚的云雾遮没了整个山峰;下边就是奶奶当年住过“家”的“蛒蛄冲”,曾经的厂棚没了踪影,坪里长满了齐腰高的杂草和冬茅,小水池不见了,小水井不见了,只有江中那两座“蛤蟆石”还一动不动地“蹲”着,鸟声、虫声依旧,山冲还是原来的模样。奶奶,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你过去住过的地方,泪水已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们想您!您在哪里?您在哪里?您在哪里?我们在无穷无尽地深深呼唤您!呼唤您!!呼唤您……(李放鸣)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