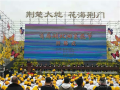布鞋记忆
方 平
“六月六,晒红绿”,在我们聂市老家有一个很特殊的习俗,即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将自家冬天可穿可不穿的棉衣毛衣,“锦帽”鞋袜,被褥床单,甚至老人的寿衣寿被寿鞋统统拿出来见见阳光,晒晒太阳,据说这样既可驱虫防蛀,又可避邪防腐,老人还能延年益寿。我没什么“红绿”可晒,今天就将出嫁时娘家给我“压箱”的一双红绣花布鞋也拿出来照照吧!
我是穿着布鞋长大的。因此,和布鞋有着血肉相连的感情。小学课本上《毛主席去安源》中对布鞋的描述也记忆犹新——“一双布鞋一把伞,毛主席来到群众中”;青年歌手解晓东“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的正走的稳踏踏实实闯天下”,那经典的歌词像铿锵誓言引起“有志的中国娃”的强烈共鸣。
据传,布鞋在我国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宫廷内、朝堂上大臣们穿着绣龙描凤的“朝靴”;皇帝皇后则有“龙靴”“凤靴”;戏曲舞台上有厚底高帮京剧变脸的“戏靴”;将士出兵打仗还有配着铠甲齐膝盖的“战靴”;朝野上下百姓日常则根据季节更替穿着布鞋、棉鞋;就连婴孩出生都有“和底鞋”。说明无论达官显贵、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庶民百姓,人一生下来就得穿鞋。而布鞋便是历朝历代人们无可替代的生活必需品,并且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布鞋还在一步步演进。小时候,常看见祖父穿的“剪刀口”布鞋,祖母的“三寸金莲”也有她特有的小脚绣花鞋,据说伯父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还穿着布面胶底行军打仗的“绑腿靴”。还有父母的方头布鞋、松紧布鞋,弟弟妹妹们的大头娃娃鞋、虎头鞋,并且颜色、图案都极富变化,穿着舒适透气,合脚送路,美观大方。
在我的记忆中,街上是没有布鞋买的,它是靠家里的亲人一针针一线线缝制出来的。做一双布鞋千针万线可真是千艰万难啊!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嫂子,我家做鞋的重担就落在年迈的祖母和上班的母亲“肩”上。她们责无旁贷利用闲暇根据亲人们脚的大小画出图样确定鞋底尺寸,把图样放在布上剪出鞋底和鞋面(鞋帮),选定鞋底布料后,一层挨着一层铺平贴上20多层,然后用一层厚厚的新布贴面做鞋底;用“打底婆”针穿上粗粗的索子一针一线纳鞋底。祖母和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她们有时用布条包扎鞋面并轧紧做成进边底,有时根据需要切除鞋底的边沿做成出边底,往往一只鞋底纳完,线迹排列错落有致,不可思议的是正面看起来是竖针,反面(鞋内)则是横针,我正面反面地摸着、看着,看着、摸着,“研究”了好久都没弄清是咋回事。接着就要做鞋帮。鞋帮的款式日渐改进,大致有方口、圆口、方口加松紧带、小方口加鞋襻。她们按事先预备好的黑灯芯绒、青卡其布、红花布、方格布等布料,在内贴两层衬布,将它们粘在一起后沿布条滚口,直线平直走针,转弯顺着走针;如果是棉鞋就更麻烦了,要在鞋底内层铺上少许棉花,绱一层伴脚底,这样穿着更暖和。为了绱鞋,祖母和母亲分工协作,先将鞋帮和鞋底前后左右对齐,用小针线固定,再用锥子“打前站”,这时还得我父亲帮忙,这既要力气,又有技巧。通常鸡叫了几遍,他们还在穿针引线忙碌着。将鞋帮和鞋底顺着锥子的针路绱起来。他们之所以这样赶工,主要是为了全家人重大传统节日有新鞋穿。
每逢年节前的早上起床看到这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艺术品”,我感慨万千,抚摸着祖母和母亲的鞋篮子,甚至将鞋篮上的流苏扯下来玩,十几天前还是几块旧布,这么快就变成了一双双崭新的布鞋,我真佩服她们心灵手巧,并且不辞劳苦。这些个艺术品每个细节都尽善尽美,连个线头都找不到,这该倾注她们多少心血、智慧和汗水哟!有时她们还匠心独运,将我们的棉鞋边沿安上羊毛,既热乎又美观。同时,幸福感爆棚,那时虽穷,但祖父母、父母好疼我们弟兄姊妹哟!这“温暖”牌的布鞋、棉鞋温暖着我家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滋润着我们幼小的心灵,教化、培养着我们坚韧不拔的性格,这些布鞋也伴随着我们姐弟一个个长大成人。记得念小学时有一天下大雨,祖父接我和弟弟回家,为不让我们打湿脚,他打着赤脚驮一个抱一个,在泥水中艰难前行,我问祖父为什么不穿鞋,他说落雨了免得把鞋打湿,话还没说完,一不小心三爹孙就跌在泥水里,半天爬不起来……这时我发现他的脚趾畸形,后听祖母说是1958年大跃进时烧窑致了残。两只脚的第二个脚趾和第三个脚趾都粘连在一起,在泥水里站都站不稳,更何况还抱着两个孩子!我后来弄清楚他是心疼祖母做鞋辛苦,因此我发誓长大后要多买几双好鞋给祖父穿,可等我有能力孝敬时,祖父已离开我们,让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而我们姐弟就从不担心落雨“怕打湿鞋”,有了新鞋上学穿,放学穿,打球穿,跑步穿,作客穿,在外面疯玩穿,跳绳也穿,天晴穿,甚至落雨还故意在水里“划”。现在想来,这种穿法莫说是布鞋,就是铁鞋也“不经穿”,加上小孩子脚“躁”鞋又长得快,常常两个月就磨破了底,有时脚趾还露出来“晒太阳”。父母看到我们如此“会穿”,无奈又别出心裁改进“工艺”,在厚厚的鞋底下贴层塑胶,既防水又防滑;有时在布鞋里加双垫底,既热乎又耐磨;甚至还在新做的棉鞋底下漆层桐油。只是后来弟妹们慢慢懂事,学会珍惜并互相谦让。记得有次姑妈给我弟弟做了一双呢子鞋面、脚踝两边安着拉链的棉鞋,好看极了,我硬说他脚小了,只有我能穿,姑妈说那你试试,结果很“蹩”脚(我脚大了),我下意识地把脚朝后一缩,说蛮合脚,就给我穿算了,硬生生地把弟弟的呢子棉鞋据为己有。当然没过多久,比我小两岁的弟弟脚比我的脚大多了,都40几码了。对于我的执拗,虽然姑妈没有办法,弟弟也不跟我计较,但直到现在我都为我的自私自利愧疚不已。
后来参加工作,大街小巷到处摆着五颜六色的塑料底鞋、人造革鞋,当然还有款式各异的皮鞋。我也想追追潮流赶赶时髦,买了一双圆头的高跟牛皮鞋。平常穿还蛮舒服,可那次在武汉作客,我穿着高跟牛皮鞋和闺蜜俊文逛街,刚起步还觉得蛮好看蛮新鲜,像跑台步样“风生水起”,可时间一长,脚跟打起了水泡,脚趾痛得好像伸不直了,我和俊文手挽手摸索移步,后来又在路边坐了一会,一双脚好像还是不听使唤,“整”得我寸步难行!心想这皮鞋虽然“高档”,但逛街穿我实在“消受”不起,还诗意般地想到诗仙李白也可能只有在梦中才有“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的浪漫情怀。硬撑着走到祖父常给我提起的汉正街的谦祥益,买了一双布鞋,结果一看是聂市古松牌,我和俊文笑得前仰后合,在汉正街买了双聂市布鞋,真好玩!但我非常感恩于它,是它救了我的“小命”。
自此,我的脚对布鞋更加产生依赖,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无论在家在外还是在北京女儿家我都爱穿布鞋,春秋穿的绣花布鞋,夏天穿的布凉鞋,冬天穿的长布靴,在家穿的布拖鞋、布棉鞋。这次清理鞋柜,我穿过的布鞋、棉鞋竟珍藏了20多双。一是尊重祖母和母亲的劳动,做一双鞋太难了,她们眼熬红了,手磨起了茧都从未在我面前叫过一声苦与累。二是我无法忘记每双布鞋起初穿时的“良辰美景”,比如母亲给我做的压箱嫁鞋,结婚那天她交给我时,我们娘儿俩抱头痛哭,她希冀我和丈夫就像一双鞋子不离左右,形影相随,永不分离。我的孩子还穿着奶奶给她做的棉鞋漂洋过海,留美、留英,并对室友夸下“海口”,这叫“奶奶”牌棉鞋,只有我们中国才有,室友Jianni(珍妮)一直用羡慕的口吻“Very good!Very good!”
时光流转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江泽民总书记及与会国家元首纷纷穿着兼具中国传统特征和西方现代造型的新唐装出入APEC会议,我突发奇想,也给自己和孩子分别做了一身唐装(母子装),配着绣花布鞋穿到婆家亲戚家作客,盛塘的两个表弟仿效我的“装束”,做了两套情侣装做结婚礼服,外加两双布棉鞋,说是古色古香既大方得体,又庄重喜庆,他们那里的年轻人也“迷恋”上了唐装配布鞋。没想到这种装束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让老报社同事“笑话”我,“既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还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退休后,我也曾尝试过“挑花绣朵”做布鞋,如此这般的贴着鞋面、纳着鞋底,结果我母亲一看说鞋底像块荞麦粑粑,我“吵”着要母亲传我“真艺”,她笑而不语,估计她一是心疼我做鞋辛苦,莫步她的“后尘”(在月子里就要纳鞋底),如今什么鞋都有买;二是了解我天生资质愚钝,不能领悟此中“玄机”;再者怕我做的“鞋”穿出去让人笑话。只是有幸的是,如今穿布鞋不需要亲人们一针一针地“螫”,一线一线地“扯”,早些年我的脚就和聂市古松布鞋“结缘”了,虽然没有皮鞋的洋气,波鞋的大气,但大俗即大雅,好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高端舒适上档次的各色布鞋既让我填补了内心的空缺和遗憾(我的祖母早作古了,母亲年纪大了,也实在做不动了),又让我过足了布鞋“瘾”,且丝毫不比皮鞋逊色,走起路来可“大踏步”前进。我买了一双又一双,打算让它们随我成为北京的“常驻大使”。我还给“古松”的杨总“建言献策”,不管是银汉迢迢星河远,还是飘飘欲仙展彩屏,都离不开一双鞋,要他们从“技术”变“艺术”,在传承的基础上挖掘整理和创新,做童鞋、和底鞋,女布襻鞋、绣花鞋,绣花布长靴,特别是内增高鞋,还有各式男布鞋、男凉鞋。促进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交融,让古松布鞋随着永巨的茶叶销到英、美、蒙古、俄罗斯。在“Made in Nie Shi”的赞美声中产销两旺,绘就生活富裕底色。今天,我又给丈夫买了一双黑灯芯绒鞋,和我的那双跟随了我三十多年的“压箱”绣花布鞋“出双入对”进入我的箱底储存起来了!
低头看脚道不远人,抬头看路则有诗和远方!
(作者简介:方平,女,湖南临湘人。机关公务员,《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各报刊杂志发表新闻及文学作品千余篇。著有小说及散文《微尘集》共两部。)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湖南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赴绥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下一篇:最后一页